
年長一輩總是說:「我哋以前無咩娛樂,但好開心,唔同你哋咁多嘢玩。」吊詭的是,城市中的小朋友是否有玩的自由?誰扼殺了小孩的空間?
五、六十後的童年,通常離不開一羣小孩在街上渠蓋彈波子、彈橡筋、上山跑的畫面。今日的兒童,能夠騰出時間遊戲的,也許沒有幾多個。在2013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出,兒童擁有遊戲的權利,每天最少要有一小時自由遊戲的時間。
「大人總是想掌控小孩生活,兒童一定要跟隨大人訂下的規條,跟隨教育制度的框架,將來才會成才。」Shelly Newstead說。Shelly來自英國,是Playwork(遊戲工作)的權威學者,她認為大人需要往後退一步,要社會上的教育工作者、社會工作者,或是父母本身,接受自己一直以來對小朋友的方式並不正確。可是這個任務,她亦覺得比起登陸月球還要困難,因為成年人指點江山太久了。
⚡ 文章目錄
隨時隨地隨意隨心才是玩
學校也許會反駁說:「學校有體育課,也有課外活動」;家長也許會反駁說:「平日放學及假日,我都有安排舞蹈課、跆拳道班、劍擊訓練,還有豎琴課呢。孩子咁多嘢玩,怎會說他沒有時間玩呢?」成年人在自由的時間,可以自行決定做什麼,但是小朋友的自由時間,卻逐漸被成年人自以為是地填得滿滿。
「教育制度有其好處,但是成年人因為外界的壓力,要確保孩子在制度內成功,忽略兒童的不同需要,一切就變得本末倒置。」Shelly嚴肅地說。
自由遊戲的重點在於,遊戲時間由孩子主導,可以隨時、隨地、隨意、隨心、愉快地做他們想做的事。
這樣的自由時間,今日的兒童,有幾多個享受得到?
城市非為小孩設計
Shelly來自英國,是Playwork(遊戲工作)的權威學者。Playwork在歐美是一門學術專科,為兒童創造最適切遊戲空間,專業知識可應用於與兒童有關的專業及服務。簡單來說,就是一羣擁有專業知識的成年人,以兒童的角度了解他們的需要,提供一個合適的空間讓小孩成長。

Shelly不是因為什麼陰影或打擊才從事Playwork的工作,她在英國的鄉村長大,笑言自己擁有很多自由,童年過得很快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被安排到城市居住。城市本身並非為兒童設計,相比起周圍都是山林河流的鄉村,市內空間肯定不足。原本的泥濘大路變成瀝青車道,小孩的活動,被局限在遊樂場之中,而且要在成年人的監視下活動。「以前在鄉村,小朋友想挖洞就挖洞,想跳水就跳水,想生火就生火──可是在城市裏,只會聽見大人們甚麼都說不可以。」
成年人之所以主導社會的運作,只是因為有較多生活經驗,並不代表可以對兒童的生活指指點點。「小朋友看世界,就是與成年人不一樣啊!」Shelly說。其實,在兒童的成長過程中,大人的角色沒有他們想像般重要。「孩子自由地與其他朋友遊戲的時候,已經在建立不同能力。」 她說。
<!–延伸閱讀:【有片:短命學校 快樂轉校記 想玩就玩】–>
在遊戲中學習生存
假如問到孩子們在遊玩時最深刻的經歷,通常他們都會提起一些「驚險」時刻。「差一點就從攀爬架上掉下來」、「差一點就從韆鞦飛出去」──這些「差一點」,最後都是有驚無險。孩子們會因為在攀爬架的最頂成功跳落地面而沾沾自喜,孩子們會因為盪韆鞦到最高點而享受到空氣掠過臉龐的快感,孩子們就是從自由的遊戲中,學習判斷周圍的環境、衡量自己的能力、挑戰自己的底線。「還未計小朋友之間的相處:與別人爭吵、要求加入遊戲、共同使用一個遊戲設施,這些也是社交技巧和能力啊!」Shelly說。

「遊樂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成為一個可以讓小朋友隨意玩耍的地方。」可是,問題來了──這樣玩,很危險啊!萬一小孩真的從攀爬架上掉下來,怎麼辦?「這就是小孩建立判斷能力的時候。」Shelly說。例如小孩會學懂衡量自己是否有足夠的腳力,判斷自己是否已經有足夠練習,假如第五層太高,不如先從第三層試跳,一步一步來。
「小孩在自己一個的時候,需要自己做決定,這才可以建立思考能力、解難能力以及風險管理的能力。」假如小朋友身邊有大人在看着他們玩,無論是老師還是家長,肯定會在他們嘗試做一些危險動作之時,已經出聲制止。
「世上沒有百分之一百的安全,有可能造成傷害不等於一定會造成傷害。安全之中帶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也是可以的。」Shelly頓一頓,再說:「假如不讓孩子冒險,他們又怎會學懂如何評估風險?」
<!–延伸閱讀:【非繁忙兒童】:他們的假期–>
遊樂場的家長也有心理自縛
Playright 智樂兒童遊樂協會有定期邀請Shelly來港授課,每次都有不少教育工作者、社工和家長報名。大人們起初上課的時候,都放不下「危險」的心態,叫Shelly哭笑不得。「他們好像覺得要將遊戲室或公園內的尖銳物品都包上泡泡紙才安心。」Shelly笑說。「輕微刺傷或鎅傷,並不是世界末日,小孩會痊癒,也會學懂下次要提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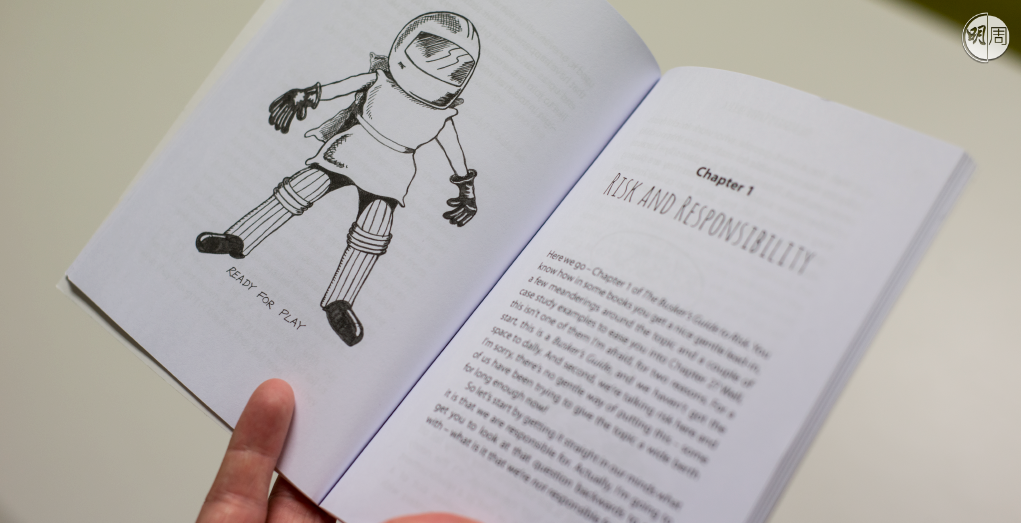
隨着大家開始明白Shelly的理念,有些家長也嘗試在生活中實踐。沒想到,最難過的一關,不是自己,而是別人的眼光。其中一對家長帶同小朋友去會所的遊戲室,然後他們就靜靜地坐在一旁觀察孩子玩耍。每逢女兒臉上出現稍微困惑的表情時,或是想要哭的時候,二人都要壓抑自己想要衝上前協助她的想法。
可是,當時其他家長在做什麼?有人在向子女示範如何玩滑梯,有人不斷將新玩具塞到子女手上。「兩位家長回來告訴我,他們二人是唯一沒有圍着自己小孩團團轉的家長,看上去就似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孩子。」Shelly說。
Shelly常常教導學生,除非小孩真的面臨真正的危險,非得要家長出聲提點或出手幫忙,否則都應該盡量「遠觀」,由小孩自己解決問題。有時候,提醒孩子小心都是多餘,一來會為他們帶來不必要的壓力,二來也應該要用小孩明白的方式來解釋,而不單止是叫他們小心。「這才是家長應該做的事。」
說到最令她鼓舞的事情,還是學生願意跨出改變的第一步。其中一位家長,終於在上課後第一次帶同孩子在下雨時去遊樂場玩。她還打電話叫上其他家長,叮囑他們要任由小孩踩水窪。「在課堂分享時,她說無論是大人小孩都玩得很開心。事實就是這般簡單,即使在雨中遊玩,也不會有人遇溺,不會有人患上重感冒,也不會有人死亡的。」Shelly笑說。
每次聽到這些個案分享,Shelly都覺得觀念正在慢慢改變。「只要有家長踏出第一步,而又發現會為子女帶來正面的影響,就會有更多人願意反思自己是否為孩子設限太多。」

童眼看世界才有「自由」
長期被成年人束縛生活和目標,缺乏自由時間的青少年,就像在壓力鍋內成長。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有數據指出,青少年自殺的數字有所上升,學生大多與家人、親友欠缺良性溝通,多宗個案都曾在遺書中表達自己長期受自殺意念困擾卻不敢告訴別人。香港理工大學近日發表長期追蹤研究報告,發現有超過一成的中學生,曾經有自殺的念頭,甚至嘗試自殺,這就是壓力爆煲的後果。
<!–延伸閱讀:【星期日人物】我們的教育之道 ‖ 張艷璿–>
教育局於今年年初公佈《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幼稚園在2017/18年開始,每天需要分別安排約30分鐘(半日制)及50分鐘(全日制)時間,讓幼兒參與自由遊戲。這個安排,對於教師而言,並不容易。
「任何需要在工作上與小孩接觸的人,都很容易以『他們』為藉口,不讓孩子冒險。」這個「他們」,可能是規矩,可能是法律責任,可能是家長要求,令照顧小孩的成年人不敢讓小孩冒險,以免需要負上責任。「孩子沒有受傷,我們就不會被告。可是成年人的工作,並不是確保小孩不會受傷,而是如何讓孩子在有限的空間內,盡可能安全和自由地玩耍。」Shelly在書中 “The Busker Guide to Risk”中寫道。
Shelly認為,教育制度有其功能,兒童在制度內可以跟隨一些目標學習。不過要從老師的教學時間拿走50分鐘,也會令老師擔憂不能教完課程。「我們不會插手老師的教學,但是會建議他們如何處理自由遊戲的時間。」今年暑假,Shelly亦有教授香港教育大學的學生,課程為期三日,還有兩日的實習課,老師要學習如何評估風險,如何觀察小孩活動。

「Playwork雖然是一項專業,但是我們是在講Childism,我們都說自己是一個Childist。」對於那些未有機會接觸Playwork的家長或教師們,Shelly有一句簡單的提議:「Chill out!」她請大家放鬆一點,「小朋友只是想玩,就是這麼簡單。人生不用那麼複雜,用童眼看世界,只需要嘗試對小孩多說Ok,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和空間。」
在Playwork默默耕耘25年,今日的教育制度好像毫無寸進,記者作為旁觀者都覺得累。我問Shelly,是什麼讓你堅持下去?她笑一笑說:「你總不能一夜改變世界,再微小的改變都是改變,我相信世界總會變得更好。」
(部分相片由 Playright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