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心安處是吾鄉。」逃難來的那一代,排除萬難,只為一處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心或者繫於邊界以上的土地,身心相隔千萬里。且聽他們的下一代,生於斯,長於斯,談那似遠實近的鄉土情懷。
第一代香港人,為了各種原因,逃難至香港。他們又各自因為不同的因緣,逃難至香港不同的角落。本來種田為生的逃難者,南逃後聚在香港邊境一帶農田,繼續耕作,他們的政治意識並不濃厚;可是,同一時間,更多政治難民逃港,包括國民黨的殘部,也包括響應中共號召回鄉,建設祖國最後卻焦頭爛額而回的熱血青年,他們無可避免帶着一輩子深沉的政治意識形態。
陳雲的爸爸即是後者。
他是華僑,回國建設,醒覺,南逃,最後落戶於粉嶺聯和墟——一個當年被稱為國民黨情報中心的「基地」。
「我的父親是個偉大的人。」
一句話鏗鏘有力。童年時覺得父親無所不能,成年後仍崇拜父親的人,卻是少數。許多人知道陳雲,都因為其著作《香港城邦論》,平地一聲雷,吸引一眾信徒。平素陳雲言詞大膽,博聞強記,談到他父親,臉上卻不自覺流露孺慕之情。

⚡ 文章目錄
一個人的戰爭
陳父是馬來西亞客家華僑,祖父開木園,家境富裕,修讀醫科。經歷日治、英殖時期,厭倦高壓統治,戰後接觸到馬來西亞共產黨的宣傳,深受馬克思主義薰陶,屬於最早一批「愛國青年」。1950年,周恩來呼籲印尼、馬來西亞華僑回國服務,陳父懷抱建設新中國的理想,毅然登上新中國派來的船隻。「說上船就去了,」果敢決斷,甚至拂祖父意,「只擱下一句,『歸國服務』。」
一上船,從此不再回首。
當年歸國華僑待遇優厚,船上供給充足,甚至供讀大學,可謂是特權階級。陳父於長沙醫學院修業期間,冰天雪地,六點起牀做早操,啃饅頭,倒小便時發現都凍成了冰渣,生活甚為艱苦。及後,到瀋陽一帶服務,再到青海工業廳待了三四年,隨地質考察隊駐醫,居於塔爾寺。後來身子熬不住高山氣候,方才申請調回廣東鄉下,靠一口客家話,回客家村尋根。其後結識妻子,當入贅女婿。
反右鬥爭,始於1957年之春,毛澤東鼔吹「大鳴大放」,邀請知識分子大膽批評政治,幫助共產黨整風,然後將幾十萬人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毛澤東所謂陽謀,」陳雲嗤之以鼻,「共產黨的伎倆,總是進行內部清算,剔去精忠和聰明人,留下更奴性的人。你看現在香港便是這樣。」當時不少歸國華僑信以為真,包括梁父在內,結果一整羣被出賣,只好逃難來港。
「他們沒有絕望,始終有香港在,就有希望。」當時邊境守護雖不嚴密,但給守衞抓到就得坐牢,於是各族各派,各師各法。寧波和上海人,風雅埋在骨子裏,據說走賄賂的法子;番禺人,好勇鬥狠,㩦刀帶棍,連邊防軍亦避之則吉;其他同鄉組織,找個引路人,碰運氣。又有說湖南籍邊防軍最兇狠,放狼犬、開槍、全部人逮捕,一個也不放,而廣東籍最仁慈,一堆只抓一兩個。
陳父於1958年左右偷渡,第一次被抓,坐了三個月勞改營,第二次跟在其他偷渡隊伍之後,看清形勢,伺機而行。先到深圳,吃過飯,靜待入夜,攀梧桐山,過燕子崖,穿過叢林與高山。遇到邊防軍,得分成六七個小隊,剩陳父一整晚踽踽獨行,擔驚受怕。彼時深圳仍是小鄉村,望着燈照那方,便是香港。
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一個人的戰爭。
聯和墟:政治中心
翻山越嶺,陳父來到沙頭角蓮麻坑,在客家村的同鄉家中躲一晚,日間搭農村菜車入聯和墟,投靠叔公。那個叔公是個受尊敬的人物,許多偷渡客逃難靠他,身邊有一幫身手不凡的好手,勢力很大。逢年過節,一幫人都會孝敬酒肉,以示尊敬。

當日的聯和墟,聚居不少客家人,大部分是國民黨餘部,曾是情報工作中心,被稱為「反共基地」。每逢十月十日,海聯廣場築起牌樓,掛起滿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回歸後,此情此景再不復見。物換星移,今天陳雲重遊故地,已經認不出當年走過的路。
陳雲清楚記得,已結業的雲天茶樓,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舊部,經常在那裏吵得臉紅耳熱,每每幾乎上演全武行。連報紙檔亦壁壘分明,一邊親國民黨,一邊親共產黨,楚河漢界,涇渭分明。
陳父來港後,再不提共產黨幹部身份。居於聯發大樓內,陳父回歸老本行,跟一班同鄉開聯合診所,掛牌當中醫。又經營生意,因懂少少英文,膽粗粗便開移民公司,由聯和墟的酒樓簽擔保,證明同鄉是廚師,便申請簽證去加拿大。「那個年代的人很有勇氣,不用學,時來運到便立即去做,」陳雲講起父親經歷便來氣,「做中國總統,給個印我就能做,共產黨塌了我便上,你以為好巴閉?政治膽量一向是老共特色,紅星印在手,誰不是官?」他侃侃而談,覺着有趣,便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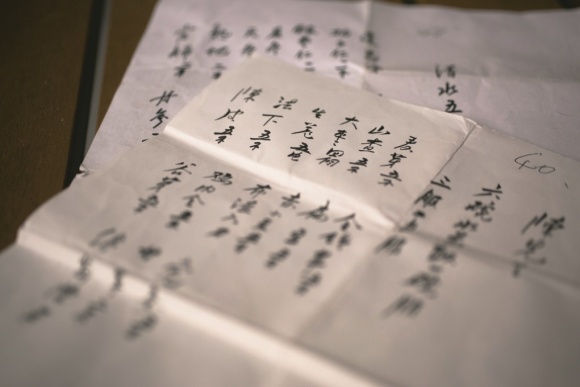
他父親未經訓練,卻在殖民地時代當過一段時間的坐堂幫辦,於邊境分局負責審問偷渡客。探聽中共動靜,收集情報,亦是他其中一樣工作。身為馬來西亞華僑,受到港英政府信任。「他是被共產黨拋棄的,身份沒有衝突。」依陳雲解讀,這是「投奔自由」,更打趣說:「共產黨專養叛徒。」共產黨自是不滿,扣起他家鄉裏的人的糧票,逼他辭職。陳父自此隱姓埋名,陳雲只能替父親不值。
「我在那個環境長大,因此看到了什麼叫地下政治,政治並不是表面見到的那麼簡單。」無心插柳,聯和墟啟蒙了陳雲,可說是他思想起點。

傷痕與希望
陳雲在聯和墟待到五六歲,後來搬到共產黨餘部為主的橫台山。每年中秋有父親老同志來訪,打邊爐間談天說地,講述韓戰、大躍進、文革的親身經歷,他瞭如指掌。「中共的野蠻統治是虐待式,一直逆向淘汱,不蠢不奸不要,直到人變成奴隸為止。」他父親早就領教過,對中共所為已經無感。
不愛黨,陳父依舊愛國。從日治時期目睹日軍殺人,驚覺馬來西亞並非他的歸宿,直至現在,他仍堅貞於未建成的理想國。「第一代的馬列主義者不會幻滅的,那是當時的信仰,」陳雲解釋,「馬列精神不夠純正,沒有為人民服務,才有災難。共產黨為一己私利行事,自有黨爭。」陳父的救國之火未熄滅,2001年中國銀行剛開設,二話不說,將所有錢存了進去。
心繫理想,身無歸處。陳父的三重身份:馬來西亞人、中國人、客家人,最後只剩下客家人而已。《留德隨想錄》中陳雲也寫道:「我們是客家人,客家就是作客的人家,居無定所的人。」他憶起童年房樑上掛着的麻布包袱,搖搖晃晃,裝滿了衣服和醫書,伴隨父親來港,亦是他流亡半生的象徵。「那是說,隨時準備遷徙,什麼都不怕,艱難、鬼神都不怕,那段日子都過去了。」勞改的日子的確過去了,但刻在心中的傷痕仍在。
聲線藏着隱而未發的哀傷,陳雲說,父親的噩夢,一做就四十年。不論父母,夜半驚醒,是常有的事。
他又寫道,「有時方言的不同,並不能將同一命運的人隔開。」聯和墟隔着麻笏河,有間客家基督教教堂──崇謙堂,找來鹽田仔的客家村民講道。大概那些逃難的客家人,沉鬱得很,便一同上教堂,聊以慰藉。陳雲說,許多人不過一般虔誠,「對客家人,重要的是族羣。」不談逃難,相濡以沫,忘記傷痛。
時光幾度流轉,人面桃花,眼前的聯和墟早已不復記憶中模樣。叔父的後代移民,白屋仔一把火燒淨了,聯和市場空置,粉嶺戲院靜待清拆,那個年代的腥風血雨褪色成一片蒼白,人事全非。


懷舊是一種對自由的渴求
只能懷舊。陳雲曾提到,古希臘哲學家希斯德的一篇神話《人類五紀》,述說人類自創造以來,歷經金、銀、銅、英雄和黑鐵時代,以金屬為喻,論人的靈性沉淪,藉着懷念昔日的黃金時代,反思救贖。陳雲認為,戰後嬰兒潮世代屬於黃金紀,現今香港處於淪喪的黑鐵時代,因此懷舊,將對現狀的不滿訴諸感性出口。
根據希臘的線性歷史觀,黑鐵時代之後是無盡的墮落。陳雲絲毫不見悲觀,「東方的史觀卻是圓,恰如尼采的永劫回歸,」如鳳凰涅槃,在毀滅中重生。「《城邦論》的信念,便是要回到香港的黃金時代。社會主義那一代是錯的,我想回到香港的八十年代,興旺、中西文化繁盛,西化得來很有品味。」
「現今這一代,反共決心很強。」身為「本土派」,陳雲對年輕人擺脫上一代包袱,重歸香港人身份,感到欣慰。「中共政府和英國私下侵吞太多人民利益,新一代應站在羣眾那邊,以香港利益為先,一些不歸邊歸派的人,最令人討厭。」他說,香港尚有許多隱形勢力的第二代,都已歸於平凡,或被收買,他當年民政事務局的職位,也是中共補償。他又透露,留學德國,英國政府又曾指令他別回香港。
父親的理想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陳雲的理想是「城邦論」的香港。他在《城邦論》說:「城邦的風令人自由」。陳雲堅信,香港未來的局面必然是既分裂又獨立。與逃難的上一代逃難一樣,陳雲不絕望,為的,是相信前方有一口自由的空氣。

Box: 聯和墟的故事
位於粉嶺北部,1949年粉嶺彭族成立聯和置業公司,聯合沙頭角、打鼓嶺一帶鄉民集資200萬、成立聯和墟。當年墟市佔地極廣,近六十一萬平方米,單室內便設有六十個檔位,成為新界最大的蔬菜集散地。聯和市場外每朝出現天光墟,農民擺賣新鮮農產品,盛極一時。2002年地標建築聯和市場丟空,列為三級歷史建築,墟市消失。其後,曾出借予《每當變幻時》拍攝,去年借予「文化葫蘆」作展覽用途。附近許多歷史建築地標,包括白屋仔、適雅餐廳以及最後一間鄉村單棟戲院——粉嶺戲院等,亦相繼消失。回歸前,聯和墟曾是國民政府人員的情報工作基地,由向氏家族的少將向前統領,斥資於軍地及聯和墟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