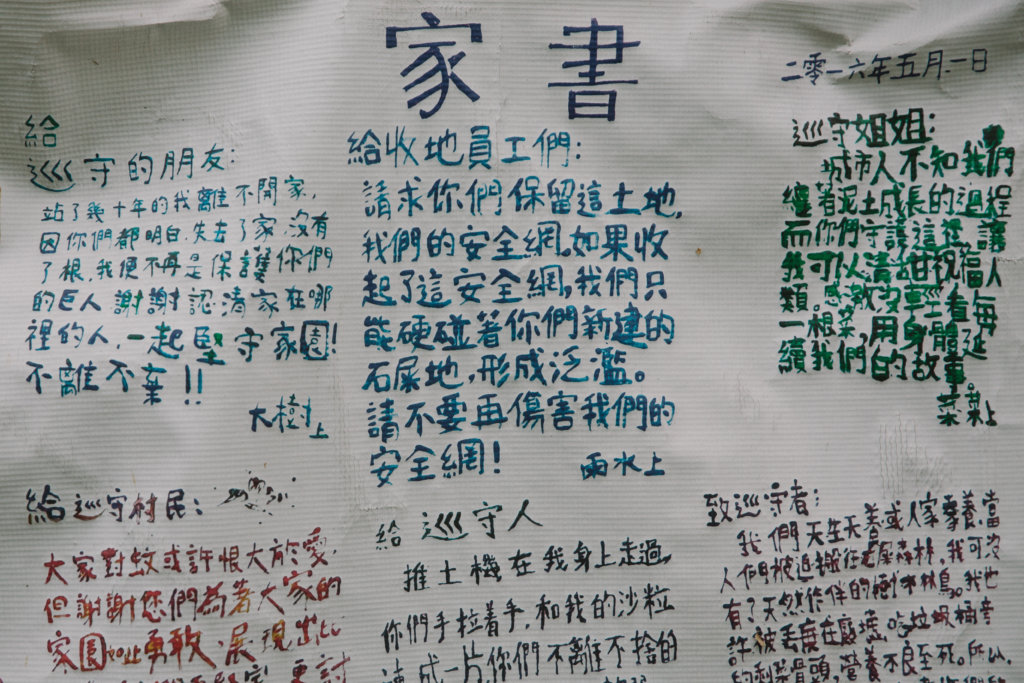星期三,下午二時,馬寶寶社區農場的農墟,擺滿蔬菜,迎來不少前來買菜的顧客。區晞旻(Becky)說,自二月疫情開始,香港人開始多吃香港菜,需求暴增,他們的菜不夠賣,於是一些朋友便向同樣受發展影響的蕉徑和坪輋農友取菜,在場內加開一個「東北菜檔」,善用空間和時勢,幫農友賣好一點價錢,「以往他們平價賣給菜統處,賣不出,菜就會彈返俾你。」
賣菜時分,也是午飯時分,菜檔後排的餐桌擺滿新鮮餸菜,誰有空便埋位進膳,這是Becky嫲嫲最喜歡的時光,人多夠熱鬧。可是,好景不會常在。這裏即將面對政府收地,大家知道是今年,但暫時還沒有一個遷出的日子,「每個農夫編了一個號碼,我們是008,政府還未前來張貼通告。」
⚡ 文章目錄
農夫竟有如游牧民族
Becky說,她和爸媽仍沒有決定去向。政府目前給予農夫三個選擇,第一個選擇是去農業園,就是二〇一五年新農業政策諮詢文件中,提及將蕉徑的八十公頃農地發展成的高科技農業園(按:全港有四千五百公頃農地,「何必偏偏選中我」)。「我們不會去,這樣會趕走在蕉徑耕田的農夫,其實真正的農地農用,是停止地產商囤積農地,阻止農地變成棕地才是農業政策。」她說。
第二個選擇是農業遷置,即是類似當年菜園村,農夫自行買地在田邊建房子,「應該沒有太多村民會選擇,因為地價比起十幾年前高出太多。」
第三個是較多人選擇的特殊農地復耕計劃,政府提出在新界北區提供十塊官地,保證每個農戶可獲分配不少於現時耕種面積的農地,不過,該計劃後來以「農地條件差,無道路讓政府工程車進入」為理由,抽起其中五幅49斗(約35萬6千呎)的農地。以現時粉嶺北及古洞北共有33農戶計算,每戶平均只可得到1.5斗(10000呎)農地,不足以維持生計。而且,這些農地位置偏遠 ,運輸和銷售都會遇上極大困難。
「這計劃的『重點』是不容許耕住合一,政府只會興建一個宿舍,每一個農戶有160平方呎的小屋,儲物空間佔80平方呎,強調不可以居住,只可以留宿,這樣我們根本無法操作,因為平常五點就要起牀開工,到晚上仍要在田裏工作。」
趁着空檔坐下休息的區太(Becky媽媽),聽見我們談到耕住合一,即時補充:「因為加設防蟲網,需要人工授粉,授粉要在早上,到中午陽光猛烈,花粉乾了就無法授粉,瓜就不會大。」農夫耕作耗費體力,累了回家休息,休息過後繼續農務,遇打風落雨,隨時都要機動地到田裏看看,即時通去水位;還有,打蟲水要在晚上進行,有時一打幾小時至九點、十點,因為蟲是晚上出來的,「譬如飛蛾就會生蟲,那就要捉飛蛾、捉蟲和捉蝸牛。」

換言之,耕住難以分離。「嫲嫲爺爺在四五十年代,用血汗才建立起這個家,這塊田也是搬不走的。」Becky說。她和爸媽決定靠自己另覓落腳之地,不過,好些地方,不是租金天價,就是租期很短,例如只有兩年或三年。當設置好灌溉系統,搭好棚,或種下一些果樹,可能要被人趕走。「所以,這些不穩定的狀態都令你很難投入耕作,很多農友都好像過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一樣。」
田園生活好過中環逼港鐵買靚衫
二〇一〇年,新界東北計劃步入第二階段諮詢,Becky當時打開規劃地圖,看見馬屎埔的受影響範圍大部分被列作「頹垣」類別,大吃一驚:「自己好喜歡的家,為什麼會變成『頹垣』?」後來想到,是地產發展商「先破壞,後發展」的伎倆—逐年收購農地,趕走村民,破壞環境,最終完成了「被規劃」的大好理由。
那時在中環上班、過着朝九晚六生活的Becky,遂決定回家耕田。「想保住自己的家。」或許,有人會如她嫲嫲般認為「農村有乜好」,不過,在Becky大學住hall時,對着四道牆不足兩星期便捱不住了。她根本不想再忍受天天逼港鐵到辦公室然後買靚衫吃貴飯,她要在生活方式上作出選擇。「住在村,身心舒坦,隨時可落田採食物或和鄰居交換食物,我不用穿靚衫,身上衣服是別人給我的。」

她只想種田賣菜,吸引人來,然後告訴大家關於馬屎埔的事。那時遇上土地保育運動的一些搞手,大家對運動有更多基礎論述,例如新界東北規劃涉及土地公義、香港農業自給率和城鄉規劃(而不是單一地談城市規劃)等更大的議題。她決定用軟性方式抗爭,辦一個社區農場,這時有人提出,這村除了夷平建樓,其實充滿可能性,像一個嬰兒,不如就叫馬寶寶,更加親切。
馬寶寶農場從源頭一條龍做起,耕作模式轉做永續耕種,銷售方式不再依賴菜統處,而是自行送菜或者自辦農墟。「之前經常見爸爸打化學蟲水,幾枝倒在一個桶裏,很臭,要關掉全家的窗,爸爸之後又會不舒服。我說,不如轉型啦。」起初,她的爸媽不贊成,因為一方面不懂,一方面快要收地,收入可能不太穩定。後來,決定試用天然蟲水,早上到餐廳收廚餘做堆肥,「我們不拿香港有機認證,它限制不能用廚餘,其實,望住農夫比認證更好,顧客不信的話,就來農田走走。」
農場給出連結其他人的空間,舉辦工作坊,教做麵包、耕種、肥皂,不強調消費,而強調生活自主,自己麵包自己做。工作坊也談及工業食物問題,讓大家思考相關問題。「舉辦工作坊前,我會給大家一小時導賞,在村裏走走,講一下發展商的手段。」例如有發展商購入農地後,會先叫農夫不用交租,「我們追着他們交租也不要」,隔幾年,就告村民欠
租、通知要收地,「好多公公婆婆,有個觀念,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也沒錢跟上市公司打官司。」

煎熬.憂鬱.火星人
她說,村民近年的生活愈來愈受煎熬,因為大型發展商早就在隔鄰的十七萬呎地盤動工,「最早七點半開始,打樁到天黑。有些人的家震裂了;有些說七八點家中的牀會震動,變成按摩牀,連我們這邊都會感到震動。」
區太說,這幾年她曾患過憂鬱症,會無故地哭,聽見鑽探和打樁聲,心會撲通撲通地跳,她甚至有過自殺念頭。「想過有什麼方法死又不會連累別人,在別人的家自殺,那間屋就不值錢了,跳樓可能會壓到別人……後來Becky的朋友介紹一些自然療法,客人也來跟我聊天,現在好了很多。」區太說。
「地產發展商可能認為,他們在自己塊地做些什麼,名正言順,別人管不着。」Becky說,這是因為香港的私有產權往往凌駕一切,地產商囤積了一千公頃農地,是大地主,就可以決定這塊地的命運。「我們覺得不是這樣,政府應該回購農地,制定農業政策,計算香港有多少人口,需要多少食物自給,鼓勵生產,這是公共利益,不是一個人買了地就決定了一切。」
Becky笑言,可能別人覺得她是火星人,「農地當然用來起樓」,所謂「農地農用」,對很多人來說,真是有雞同鴨講之感,但她一直不厭其煩地強調,希望有更多人變成火星人。
終於,去年六月,反修例運動期間,她遇到了火星人。
那時,很多年輕人在現場抗爭,她和朋友想到的是:「看見這些努力令香港變得更好的人,希望他們能吃到來自這土地生產的食物。」於是,他們走到田裏,看看有什麼材料:茄子當造,就做茄子醬塗麵包;還有做飯團、番薯糖水、雞屎藤……
食物做好,他們就出車到現場,找到好時機或較安全的地方派發給抗爭者,「有一次,椰菜花當造,我們就做了椰菜花湯,在防線外派發,那時晚上十一二點,天氣冷,他們喝着熱湯,覺得好surreal(超現實)。」他們把食物親手交到抗爭者手中時都會說:「這些食物來自東北,香港人,吃香港菜。」聽罷,抗爭者點點頭,便珍惜地捧吃着。
「我相信,抗爭好像播種,一場雨,芽爆出,社會慢慢會改變。」

爬上推土機的人與哭泣的南亞裔保安
二〇一六年四月至六月,馬屎埔長出了一座木頭做的「瞭望塔」。它立在恒基所收購的十七萬平方呎農地上,與它對峙的,是旁邊一部推土機。推土機上掛滿了各式標語:「守田!中止原址換地!保衛東北!反對迫遷!」
這是馬屎埔村民盧永燊、Becky和區太其中一場難忘的抗爭,他們腦海有着以下畫面:因為香蕉樹被推土機夷平了,有一個外來的農夫教我們在附近拔起香蕉樹的根,那就是樹苗,於是我們七手八腳搬來一棵又一棵樹苗,重新在現場栽種起香蕉樹。
在村口紮營逾月的「守田小隊」爬上推土機喊口號,推土機司機卻照樣開啟引擎。保安架起鐵絲網圍封農地,用燒焊固定鐵絲網,村民一次次用水撲熄燒焊,保安又一次次在村民腳邊繼續燒焊。
「後來有一隊壯碩的南亞裔保安站在最前,我們又有一隊女生走到他們面前,她們告訴他們為什麼要在這裏抗爭,發展商如何對待村民,後來說到連保安都哭了,放軟了手腳,保安阿頭只好換了另外一隊香港保安。後來,南亞裔保安說他們的家鄉也耕田,也曾被人收地,這次不知道要來幫地產商做這些事情,然後說,明天不會再來。」Becky說。
「有一羣外面來的朋友幫忙(守村),我真的很開心,但不希望他們被捕或出事。一次,他們想剪鐵絲網,我丈夫幫忙,結果被保安箍頸,後來被控告刑事毀壞,要守行為。幸運的是,外來的朋友沒有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