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動物,有一種奇妙的關係。當你已不再相信人性時,後巷中小貓的一聲叫喊、在綠坡上與牛對望,甚至只是看着山間野豬媽媽帶着小豬們覓食,都能溫暖人心,令人覺得這個世界依然有着純真。文學中的動物,一直都是存在的,以主角形態出現,又或只為了襯托人類,成為某個寓意的載體。動物文學讓我們反思自身,亦反思當下,城市、人類、動物,如何能共存共生,讀過了關於牠們的文字,動物們的生存狀態,或是人類生活的隱喻,或是牠們本身在城市中面對的問題,讀着,甚至已分不清自己是貓、是野豬,還是蒼蠅了。

⚡ 文章目錄
城市中的動物文學
要在香港找尋「動物文學」,的確不易,在這個高度都市化的地方,動物好像不太重要,我們關心家中飼養的小貓小狗,卻無暇理會流浪於城市夾縫中的牠們,更莫說是山巒中的鳥魚昆蟲。偶爾在文學中讀到的動物,也只是故事的陪襯品,是主人翁的寵物或生活玩伴,對於動物的境況,甚少着墨,即使是打着以貓眼看世界、夏目漱石的《我是貓》,也不過是透過貓眼睛看人性的百態,對貓自身的生存狀態,亦未必有很多描寫,「動物文學應該是以客觀的文字,來描述動物真實的面貌,寫動物的處境和活動。」作家張婉雯說。


收錄在《微塵記》中的《打死一頭野豬》和《老貓》,當然有着動物的身影,野豬就如鬼魅,在城市人的生活中出現,以豬喻人,亦以人寫豬,兩者的狀況,互為對照,寫《打死一頭野豬》是源於一單新聞,一名南亞裔男子被警察擊斃的案件,短篇中主角好友阿稔的爸爸,別人說是瘋子,被警察「打死了」,而他某次碰見,從山上跑到城市來的野豬,被人射殺。他與牠的處境,何其相似,都是一個關於「他者」的故事,「這是少數族羣和野豬的共通點,又如國內作家陳應松的作品,寫城鄉之間的拉扯角力,人類從鄉鎮來到城市,他們同樣是他者,被城市排斥。」
被邊緣化的動物們
太平是一頭狗,一直跟着主人,從深山內的老家,一直走到城市打工去,即使主人毒打牠,把牠賣到狗場去,牠也能死裏逃生,再次回到主人的身邊,然而當主人在工廠內,嚥下最後一口氣時,太平真正的逃出來了,回到老家。農民工和狗,在陳應松的《太平狗》中都是被不受歡迎、不受保障的一羣,「這作品揭示的是內地城鄉的差異問題,從狗的角度來看,城市是否一定更美好?又如蒙古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作品,他在草原生活,長時間與動物共處,寫出來的文字,很有真實感。」
她說格日勒其木格.黑鶴愛獨自行山、露營,寫自己在野外中的故事,在漆黑中,不知名的動物從頭頂近距離飛過,清晨醒來,發現原來是一隻大鳥,「大鳥能攻擊他、啄食他的眼睛,但最後只是警示他,到了第二年重遊舊地,大鳥再次在空中掠過。故事情節看似簡單,表達的就是人與動物是平等的,在山中,人根本無法保護自己,尤其是在黑夜。對城市人來說,這是一種新的思考方式,動物的求生方法很強,而人類呢?」
生存共同體
走進大山大河,能發現自身的渺小,香港沒法產生出這種以動物為本的「動物文學」,也許是生活形態使然,面對家中被馴養的小貓小狗,我們高呼可愛,甚至自稱為奴,但面對流浪貓犬和山中動物,城市人即厭惡亦恐慌,「城市人寫動物,很多時局限於貓狗,當然,牠們是我們重要的生活夥伴,但題材其實可以更闊。」中篇小說《潤叔的新年》中的後巷貓,是離職同事的託孤,潤叔初時只為幫忙,後來即使放假也要拿着魚骨回到後巷,貓和人逐漸建立關係,而餵貓卻又勾起了他與母親在鄉下時與貓生活點滴。後來貓不見了,原來躲在將被拆卸的舊樓內產子。社區重建與流浪貓的生存與生活,在張婉雯的作品中,是經常觸及的題材。

這或許是跟她個人的取向有關係,寫作以外,她也是動物權益團體「動物地球」的幹事,小說中的動物,不是配角,而是主角,動物權益的信息,大概也能透過她的文字,直接進入讀者的心坎,「我們和動物坐在同一條船上,是利益共同體,牠們有事,我們也不會好,土地大家都有份,但城市設計偏偏沒有考慮牠們。」對她來說,文學既是目的,也是手段,以自己最擅長的方式,接觸更多人,讓她的信念,感染冷漠的城市人。
古典文學中的小獸
張婉雯說得對,城市人對動物的認識,大部分只停留於貓狗,更莫說是野生動物了。葉曉文的著作《尋牠》,很多時都被人聚焦於動物繪圖上,但她筆下的,除了圖,還有字,畫出動物的形態,每篇還有文字,詳述這種動物在哪些典籍中出現過。動物在文學中,能夠以幻想中的小說主角形式出現,當然也能夠以歷史和自然生態的角度存在。


「守宮砂」這種女子守身的標記,在武俠小說看得多,葉曉文竟然提及,只因她從晉代的《博物誌》中,讀到守宮砂的傳說,而這個傳說,就被她寫在「中國壁虎」這一章內,還寫着以壁虎製作守宮砂的殘酷,從而印證古代社會對女性貞潔的迷信。葉曉文在大學時讀中文系,接觸過不少描寫動物的古典文學,「有一課『神話與文學』,很多文學都有動物的形象,例如女媧和伏羲,都是人面蛇身的。又如《山海經》中,也有寫過大頭龜,說『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其名曰旋龜』,雖然不能百分百肯定這種旋龜是否就是大頭龜,但讓我充滿聯想。」
走遍山野 尋找那個牠
在寫作中,她寫動物,亦寫古典文學如何呈現,但文學畢竟不是科普,對動物的描繪,也不是以精準為先,為了寫《尋牠》,她跟科學家或動物學家朋友走遍香港大小山脈、山澗,但觀看動物的視覺,卻是截然不同,「他們看到的是動物的形態、數據、習性,我會想起這種動物的文學意義。」小時候,她讀加拿大野生動物學家西頓的作品《動物記》,西頓是作家,也是一位畫家,葉曉文翻着這本舊書,一邊指着書中的插圖說着,「這些關於動物的故事,寫的是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動物在不同的環境中,如何生存,而人類的角色,往往就是加害者。」

葉曉文是作家,也是讀者,寫花寫動物,是性格使然,小學時,她已讀完《動物記》的整個系列,那隻為了自由而跳崖的黑馬,深深印在她腦內;還有那隻遠離自己族羣,飛往他鄉尋找擁有同樣意志、一起鍛鍊飛行技術、《天地一沙鷗》內的海鷗強納森,這些動物文學,充滿寓意,比喻人的境況,同樣也是動物與人、大自然之間角力關係。
動物文學分類
關於動物文學,作家、影評人鄭政恆指出,可以分為四類,第一類以動物作為寓言,例如《伊索寓言》和《動物農莊》,有人生寓言或政府宣言,諷刺社會;第二類是變型類,把人變成動物,例如《西遊記》和卡夫卡的《變形記》,是一種狂想、奇想;第三類則是以動物視覺來叙事,如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和老舍《貓城記》,這種動物文學旨不在說動物,而是透過動物反映當時的國民性、政治冷漠、對時局的無助感等;而最後一種,就是故事中出現的活生生的動物,以動物作為主角,如張婉雯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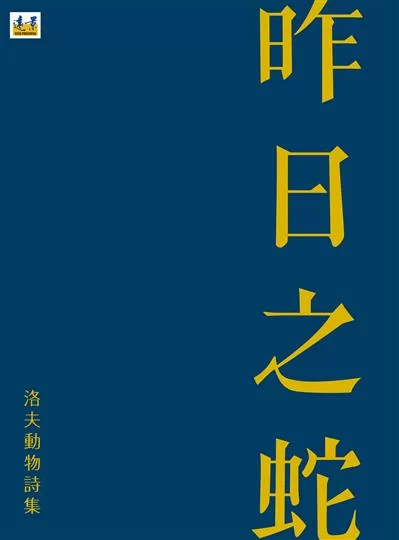
在動物文學中,不能遺漏的,還有詩歌,不少詩歌都有動物描寫,台灣詩人洛夫最後的作品《昨日之蛇:洛夫動物詩集》,就收錄了四十一首關於動物的詩,「詩講究意象,意就是心意和情意,象是物象、形象、視象,動物詩就是透過動物的象,來表達意。寫三文魚,是運用三文魚充滿生命力的習性,把意念表達出來;又如寫長頸鹿,描述望穿秋水、瞻望歲月的意境。」
以不同角度 觀看社會
作家的視覺,對於寫作,尤其重要,是遠觀或是近看,以第三身或是第一身,都有不同的效果,鄭政恆解釋,近距離觀察動物的作家,葉曉文和劉克襄就是此類,劉克襄寫《虎地貓》,是他在嶺南大學做駐校作家期間,對貓們的觀察,每天用上數小時,就只是看貓,拿着相機拍貓,分析牠們的地盤分佈和生活作息,寫貓也寫貓與校園內的人的互動。而以動物作為第一身的作品,則有劉以鬯的《天堂與地獄》,以蒼蠅之眼,看茶餐廳內人生百態,反照人類生存的本質,「人不能飛,但透過蒼蠅,能游走於不同的地方,能躲藏着,竊聽着人們的對話。這些昆蟲在人類眼中微不足道,其實卻是與我們共存的,即使是厭惡性動物。」

香港的都市文學,是璀璨的,但動物和自然文學,卻沒有台灣和國內的成熟,鄭政恆認為這是與生活空間有關,「香港綠化地不多,但其實動物也是無處不在的,舖頭貓、昆蟲、寵物,鍾國強的《家族》,寫兩代狗,主人救狗回來,媽媽卻食了狗,對上一代人來說狗是食物。不同時代和空間,就如出現不一樣的動物文學,動物在文學中的角色不斷改變,這其實也反映出時代。」而這個時代、在香港,動物所面對的,同樣是與人類的張力,被驅趕、被虐殺、被誤解,與那個「被食去」的時代,根本沒有分別。
後記 ── 書寫動物,總是帶着愛
張婉雯的《潤叔的新年》、劉克襄的《虎地貓》,令人感到他們對動物的愛,一種帶有憐惜卻又感慨都市變遷的感情。故事中的動物,似乎都有着主體性,是作家的無限聯想,或是動物本身便是靈巧如人,甚至比人更懂洞察眉宇間的憂戚。看着街貓愴惶的眼神、飛鷹在山中飛翔時如炬的目光,就知道文字並沒有說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