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展緯今天最為人熟悉的,可能都跟椅子有關。保安員的椅子,惠康收銀員的椅子。社會成為了他的創作版圖。藝術還是運動,對他而言沒有非此即彼的必要。他告訴攝影師使用中的大紅色憤怒鳥背包,可視為他的標誌,然後笑得開懷。原來那本來是人家送 給女兒的背包,因為當時幼兒園有指定書包,他打算用過後再給女兒,讓她去用爸爸用過的東西。誰知女兒大了,背包也舊了,只有自己繼續去用。透過物件盛載意念,可以由他最原初的藝術觀念說起。

⚡ 文章目錄
高據山頭的日子
程展緯唸中大藝術碩士時,正值回歸前後。他形容當時藝術的氣氛並不落地,回歸議題明明火熱,香港人身份亦可算是聚焦議題,可是身邊的人都沒有談論回歸的意識。「記得回歸當日,正在開一個名為《鬼遇》展覽的會 議。陳育強策展,於Para/Site展出。十分平淡。」連畢業論文的題目《探討繪畫中的二元對立,游離於幻象界與物象界》,他說今天聽起來好像也不知在說什麼。這些表像上看來只 是藝術形式的探討,對社會沒有多少直接的回應,「然而我們都是歷史中的人。這種冷漠疏離某程度也就是歷史的一部分。」當時還在租住中大附近的赤泥坪,畢業後繼續在山頭之上,遠離塵世。
跳出畫廊夢
當時的程展緯,對物料的運用最感興趣,最多使用的是雙面膠紙。然而一次前往澳洲的駐留計劃,在文化衝擊下引起他的反思。「當時落機第一件事,是要去買雙面膠紙,但原來澳洲是沒有雙面膠紙的。」突然感到自己的藝術創作方式原來如此脆弱,就想不如放開一 點,以可接觸的物料為素材,「不如用人?」 他當時想,最簡單直接的可能是攝影。「陳育強當時常強調一種減法,幫助藝術進入社會。 一切多餘的都取去,令作品成為最純粹的狀況。這想法令我發現,物料不一定要把持,主題隨時可以轉換。」這是形成他學習從生活取材的開端。
二千年香港未有太多畫廊介紹香港藝術家,又到了紐約PS1藝術中心駐留,自言入世未深的他貿貿然向大畫廊介紹自己的作品。縱然失敗,經過一年觀察,卻發覺藝術原來有更多可能。他們幾位香港藝術家,更發起十四國家的聯署信,要求駐留的藝術空間開放予公眾參觀。也是那一次,認識了今天的太太。「回到香港,藝術空間發表創作仍然那麼艱難,唯有闖出去。」公共空間創作由此而起。

(中)為作品《天氣報告:液化陽光》,他曾去信台北警局 借水炮車做作品,信中由下雨 的意象,連繫到港台抗爭與政 權暴力。
(下)作品《解款車》為收紙皮老人切割整齊的貨物,他曾 放到Art Basel展場上對藝術市場提出詰問。
社區漫遊者
那時剛從紐約回港,在土瓜灣牛棚對開租住唐樓。「敏感度或者正是這樣形成的。我是由山上讀書,再到走進城市看見種種不同。」水坑口的彩虹天橋,是他早期社區藝術作品,「雖然說那是英軍登陸的位置,但對我而言感興趣的是,那天橋頭尾都看不見起點和終點,不正 是跟彩虹的特性好像嗎?」
原來每天把天橋換上不同顏色要由早上 10時到下午5時,一整天的工作令他察覺人與橋的關係。「附近幼兒園的學生放學,會問: 叔叔,下一次是什麼顏色?」小孩可能正值學習顏色的年紀,由不理解他的行為,到習慣顏色的轉變,又或者引起種種疑問。「這正是概 念藝術第一層的表現。當你在簡單直接實踐的過程中,卻同時會發生許多複雜的事情。這對我而言是很有趣的經驗。」他以Flaneur(漫遊者)定義當時的自己。
學習資源分配
由觀察到真正介入,仍有一段距離。到紐約前,他在唯一一年全職的教書生涯中,不 單教美勞,更教常識,還當起班主任。從中,他掌握了一種洞悉環境狀況的能力,從而激發起改變不理想環境的意欲。他發現要令小朋友聽話,就要用最少的獎品達到效果,唯有絞盡腦汁。試過畫怪獸圖畫獎給乖小朋友儲存,最多的才有獎,「他們總有人會弄丟一些」,他狡黠地大笑起來,「又或者一開始就一次過給兩隻出奇蛋一個乖的小朋友,其他人就整堂課都 好乖。一定要一次給兩顆才有效果。」他形容當時的自己什麼都不懂,這是從山上下來的人,會想到的資源分配方式。
然而,他後來認識到一些學生的單親家庭等背景,造成他們根本難以學習的處境。「那時才一級一級地理解到人們的真實生活。有些窮到連飯錢都沒有。」在資源不足下,他學習到放棄。問題卻日復日的存在眼前,他連送沒有家長接送的學生回家,也被校長指責,不被允許。累積起來的無力感,令他無法再支撐下去。
一場概念的戰爭
在過往訪問中,程展緯曾說過:「藝術家要洞悉整個社會運作的框架,找到自己應該站在什麼位置。」在選擇位置前,社會狀況不可能再置身事外,對不公平制度不期然作出反應。慢慢遠離原初保持距離感的「漫遊者」 狀態。「生活在城市中,為何會一直保持距離呢?」當時的思考,正跟2006、2007保衞天 星、皇后碼頭事件碰撞。「他們製造了許多論述,包括碼頭跟示威歷史的關係、殖民地歷史的關係、怎樣的建築等。論述之中,令更多人跟它有關係,從而進入運動。」
公共空間的概念,亦由是進入了他的藝 術領域,於《明報》合作「騎劫遊樂場」專欄,由時代廣場的休憩空間開始,廣場的公共性亦開始與社會運動結合。2009年他更成為活化廳發起人之一,嘗試連結藝術跟社區的關係。「當年手紮花牌的黃師傅是我們首位駐場藝術家,我們找到他正因為他在深水埗被逼遷。」抗爭政治跟手藝在那種時刻無奈地結合起來。然而程展緯的女兒出生,已遷入大埔的他只能回到自己身處的社區出發。
我們都是打工仔
「當時連結的意識開始受重視,會思考如何在下次風暴前連結起來。大家會想到底『大家』是什麼。」然而這一切都不及2012年匯豐地下的佔領中環對他產生的影響。「我本身沒有如資本主義或馬克思之類的知識系統,但當時製造了許多討論,不同能力的人亦加入, 我學習到一種資本主義想像以外的可能。」
「共享」概念開始流傳,激發起他往後更多創 作,如大埔的共享籃球等。「那十個月駐留經驗其實慢慢實踐了一些東西,影響了一些人。近來我家樓下的小巴站就放了盆植物說要共享,自由定價的餐廳也陸續出現。」不單是抗爭結果,倒是對生活的實踐給他帶來更大的鼓舞。到雨傘運動,程展緯已經在他的保安「爭凳仔」行動中。「現場不認識的人互相關顧, 那一刻給予彼此安全其實好簡單。」然而前一 天晚上撐學生,早上他經過紅隧就回理大當保安,那天正是他第一天上班,「好像精神分 裂」,他說。
仍然在社區為基礎建立連繫的他,見意識形態的分裂還是無可修補。他近日為收銀員「爭凳仔」的行動,更提出收銀員和顧客只是上班和下班的打工仔之別。「透過這種身份是否可以重新連結起來呢?這其實是想要重新洗牌,找出一種新的共同點。其實我們許多人都在想的是,政制的民主化以外,生活的民主化該如何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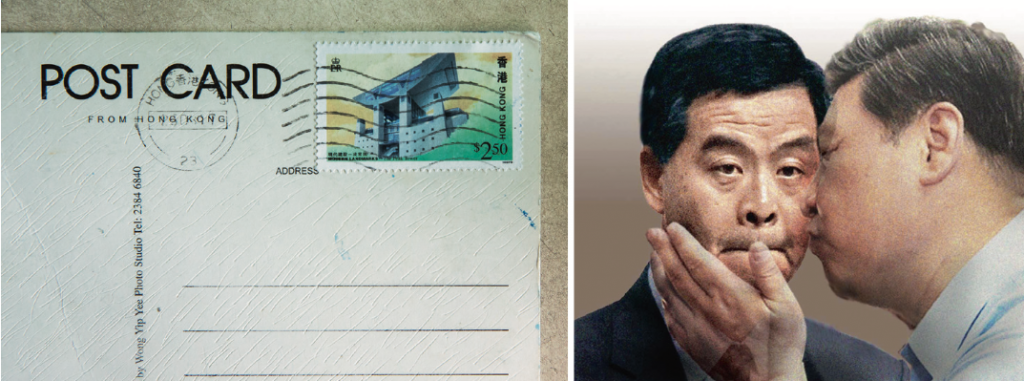
(右)去年獲提名藝術發展獎,他繳出的作品,沒有選上。他說今年選上是因為今年不需藝術家自行繳交作品。
《撿來的時間,撿來的故事─ 由一封 廿年前的信開始》
日期:即日至8月12日
地點:凱倫偉伯畫廊(中環鴨巴甸街20號地下)
票價:免費
查詢:2544 5004
(部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程展緯,1972年生於香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碩士課 程。由早年以物料應用為創作主題,到城市漫遊者般體察社會,近年更透過藝術形式介入社會以至回應政治議題,超越藝術形式和限制,同時打開生活想像。海外展覽和駐場包括紐約 PS1藝術中心、 英國Blackburn Museum and Art Gallery、日本福岡亞洲美術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