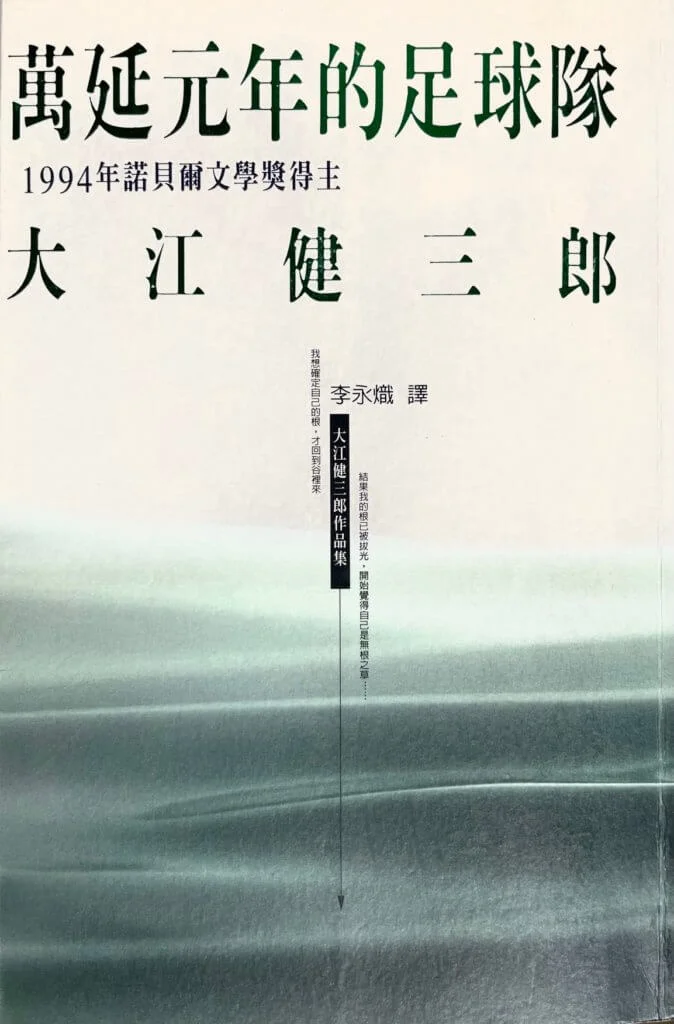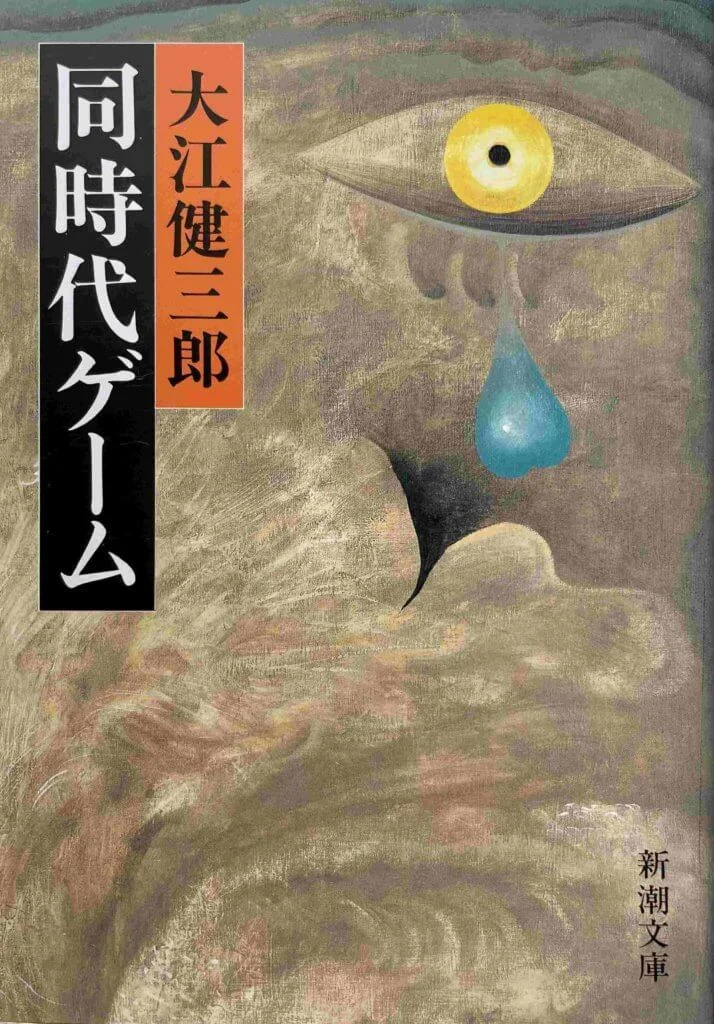對大江健三郎來說,小說不是寫實的工具,而是虛構的裝置。無論是個人體驗、社會事件、政治行為,還是歷史問題,小說的功能也不是單純的反映或者直接的批判,而是通過虛構的手段,把當中的要素加以分解和重組,成為可以理解和把握的神話。這裏所說的神話,不是指狹義的、充滿想像色彩的古代神話(但並不排斥),而是廣義的、聚焦於特定象徵和結構的故事。毋寧說,每一個作家都在創造自己的神話,但大江健三郎最為自覺,而且最有系統。
說神話可以理解和把握,不是說神話只是某些內容的代號,可以化為簡單直接的表述。如果是這樣,神話就沒有存在價值。相反,神話具有多義性,它給予人的是象徵上的和結構上的把握。要將這把握化為思考和判斷,還要一番解讀功夫。作者的工作是前者,而讀者的工作是後者。大江同時扮演作者和讀者,在小說中閱讀其他作者的作品,也閱讀自己的作品,形成了神話的多重建構,試圖迫近核心的謎團,亦即那稱為靈魂(或神)的東西。

在《空翻》中,「師傅」和「嚮導」的角色,不但是教會裏的「救世主」和「預言家」,也代表著無意識和意識的關係。大江有沒有鑽研過深層心理學,並沒有關係。他通過文化人類學和結構主義,接通了戰後由榮格確立起來的心理分析方法。師傅進入巨大的冥想,在幻象中和不可名狀的終極之物(暫且稱為「神」)對峙,發出無法理解的囈語。用心理學的語言表述,就是在夢境中與深層無意識發生接觸。要把混沌的無意識提升到意識的表層,我們需要的是語言。嚮導的工作就是運用語言,把師傅的冥想轉化為可以理解的、意義清晰的內容。
這是大江對於新興教會如何確立教義的描述,但也可以視為小說創作本身的隱喻。他曾在散文中引述英詩翻譯家深瀨基寬所說的「界面」(interface)概念,也即是在文學創作和閱讀上,「內部和外部有效交流的特殊場所」(或「內在靈魂和外在現實兩相對照」)。嚮導所實現的,就是那個「界面」。沒有這個「界面」,一般人無法深入那個無以名狀的「內在」。難怪當師傅形容自己的使命是不斷「閱讀」一部大書時,畫家木津立刻脫口而說:「那本書的書名不是《空翻》嗎?」這個自我指涉意味深長。
大江探索信仰的《燃燒的綠樹》和《空翻》並非憑空突出、全無依傍,而是嵌入於他一直致力經營的神話系統中。信仰和神話之間的樞紐是「靈魂」和「地方的魔力」(用文化人類學的名詞就是「場所的力量」)。兩部小說的場景也是四國森林,相隔十五年的兩場教會運動都加入了當地的神話傳說系譜。森林家鄉最早進入大江的創作意識,是在一九六七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在這部小說中,首次出現(蜜三郎和鷹四兩兄弟)回鄉的情節,並且把地方反抗運動的歷史,追溯至萬延元年的農民暴動,以及持不同立場的曾祖兩兄弟之間的衝突。但這只是歷史傳說,還未算是神話。
到了一九七九年的《同時代的遊戲》,大江的森林神話工程終於全面展開。從明治之前的反藩暴動領袖龜井銘助,一直追溯到五百年前,帶領一羣年輕武士脫離海邊藩國,從河口逆流而上,進入與世隔絕的森林深處,並以炸藥爆破堵塞去路的大岩石,進入未開發的原始天地的始祖「破壞人」。在森林中定居和開墾的破壞人和同行的創建者們,生存了上百年,而且身體逐漸變大,成為巨人,是完全地神話化的存在。而他們創造的獨立於國家政權的共同體,被形容為「村莊=國家=小宇宙」。小說敘事者是一位中年歷史學家,接受了父親=神官所委派的、書寫當地神話和歷史的使命。從此以後,大江在這基礎上不斷虛構下去,形成銘助、銘助媽媽、前義哥、義哥(隆)、新義哥(隆的兒子)的承傳,以及地形學上諸多象徵,如大岩石、大楊樹、「在」、「鞘」、公館、天窪(人工湖)、湖中島、島上大扁柏、圓筒形教堂(音樂廳),還有多種儀式和習俗,如童子螢、御靈祭、死者之路、自己的樹等。這些神話和傳說內容,是長達三十多年的累積和演變的成果。
我們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小說=神話=共同體=小宇宙」。大江不只是以小說處理神話、表現神話;他的小說本身就是神話裝置。不只是當中關於古代神話的部分,連同當代的現實世界的部分,也是置於神話結構之下予以理解和呈現。這就是為甚麼大江人物(特別是中後期)的心理狀態,跟一般現代小說人物不同。一般現代小說刻劃的是「現實中的人的心理」,也因此可歸類為「心理小說」。日本的「私小說」被稱為寫實主義,就是這個意思。大江人物的心理真實性不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用平常的角度看,可能會覺得他的人物很奇怪、不自然、不真實,因為他著力刻劃的心理,不是個人心理,也不是社會心理,而是神話心理,也即是深層心理。
這並不是說,大江的神話心理學與現實脫節,停留於靈魂的、形而上的層次。相反,大江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深層心理折射到當代社會政治問題上,達到神話的同時代化。不是過去式的、成為歷史材料的神話,而是現在式的、動態的神話。「村莊=國家=小宇宙」的神話,是對當代國家主義的持續批判。小說這個裝置不是靜止的,而是行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