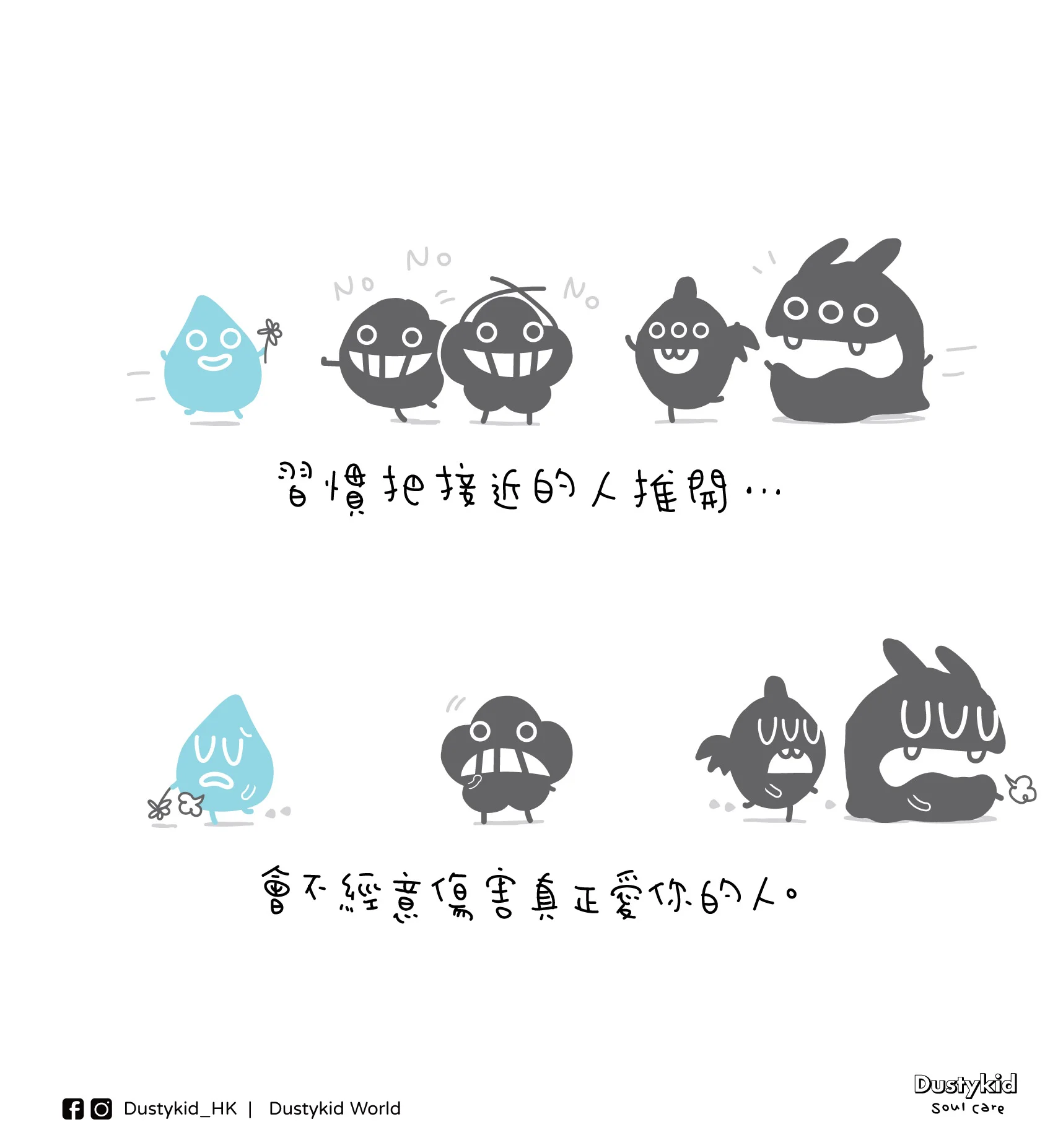從今天起至本周末,即1月17-19日,大館當代美術館將舉行一年一度的《BOOKED: 香港藝術書展》,參展單位分別來自本地、亞洲和國際,將展出(和出售)各種藝術書籍、藝術家製作的書籍和雜誌。同場還會舉辦講座、對話和展出特別展品,包括各國社會運動示威的雜誌。我最近便向張伊婷和曾智愛怡編輯的《Pillow Hands, Heavy Feet》提供稿和照片。該份雜誌的主題是「在幽默與憂傷、憤怒和異化之間擺動──廿三位供稿人……反思現時社會運動中的藝術策略,以及我們回應或處理集體改變的方法。」
拙作如下:
我在11月15日和17日到過理工大學。在11月16日晚上,警察與示威者在校園正門展開了激烈的攻防對峙,地點在平日交通繁忙的柯士甸路和漆咸道南交界,這裏是理大和香港歷史博物館、嘉諾撒聖瑪利書院,還有人民解放軍槍會山軍營為鄰的地方。
與此前的示威者/警察相遇的情況不同,示威路障和警察列陣在十字路口延續數天。警察從街道對面發射了一輪又一輪的催淚彈,配合兩架水炮車(或者某些人以本地粵方言輕蔑地稱為警察的「老婆」),多次噴出中含有獨特藍色染劑刺激性液體。對峙演變成大型圍堵,警察以近乎戰爭的隊型進攻與退守,而示威者則以汽油彈和湊合而成的投石器發射石頭防守。示威者最初佔了上風──他們佔據了有利位置,能俯視校園入口和十字路口,也控制了連接大學與港鐵東鐵線的架空行人天橋。當警方於11月17日封鎖所有校園出口後,圍堵很快便告終,而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有些示威者自願離開校園(並令自己隨時被捕),另一些則逃離現場。
這些照片記錄了圍堵事件的其中一個角度,就是示威者與警察之間的水戰。除了為人熟悉的黑衣,示威者還穿上了膠雨衣,以保護自己免受警方以水炮車發放的刺激性液體影響。示威者碰上了液體後,皮膚和眼睛都感刺痛。義務醫護以生理鹽水為中水炮者沖洗,然後收集樣本作分析用—政府說催淚彈和藍色水的化學成分因為「警務行動原因」而不能公開。
以下的照片是眾多刻劃理大示威者與警察之間「水圍城」的其中一幀作品。我最終在11月I7日午夜前,即警察封鎖所有出人口後,以自己的記者證離開理大。我打算返回上環的家,但所有鄰近的公共交通已停駛,於是只能向西區海底隧道進發。尖沙咀、佐敦和油麻地的街道儼如戰地,因為城中的年輕人都湧到這裏,希望幫忙「救救理大」。我不急着回家,所以繼續拍攝和親眼看清街上情況。那天的白晝與黑夜,我看到了很多令人不安的事件*,自己也經歷過一件這樣的事情。
走在金巴利道時,一名年輕女士上前向我展示自己的手機,並問我可否和她走到柯士甸道,那裏正有警察嘗試進入一間食肆拘捕示威者。示威者通常會請新聞界見證警察行動,而當時那區只有我是新聞界的人。我很快便同意到那邊去看個究竟,但只走了50米左右,我便被指向我的強光照得暈眩。我在兩輛汽車之間盤旋,然後走到行人路上,瞬間便被五名身穿黑衣的警察包圍。其中一位非常激動,把警棍指向我的頭部,不斷大呼「香港身份證、香港身份證!」我馬上拉下自己的催淚彈(紙)面罩,然後舉高雙手,說明自己的身份證放在背包內,而我將會除下背包再把它找出來。(這種情況下,可以很寬鬆地被理解為「反抗警察」,所以不建議作出任何未經解釋的動作)。幾秒後,當他仍然高呼「香港身份證」之際,他突然捉住了我的頭盔,然後猛力地把頭盔往後拉。幸而在下頜位置的鈕子是鬆開的,未至於令我連頭帶盔地被往後拉扯,否則可能造成嚴重傷害。我想那位警察看到我的白髮後,知道我並不年輕,頓時感到意外。另一位較冷靜的警察同僚介入,檢查我頸上掛着的記者證。這次遭遇只維持了幾分鐘,儘管我腦中想到可能出現進一步暴力和/或拘捕,我卻出奇地冷靜和接受。未幾,整件事就像它開始那樣突然結束了:我被盛氣凌人地揮手驅散。
我馬上遇到另外四位記者,加入了他們。我們緊隨那位警察,他不斷轉身,以強光照向我們和我們周圍,嚇唬說示威者可能出現突襲。街上的緊張情況可怕非常:年輕的警察和年輕的示威者受扭曲的對錯觀念鼓動,互有進攻與防守,還有互不信任的悲哀。
然後,因為金巴利道已被封路,我們無法前行,於是攀過後巷樓梯到了尖沙咀警署,那裏又是另一場示威者投擲汽油彈和警察發射橡膠子彈的對戰;另一件需要見證的事情。
*見2019年12月5日《明報周刊》的本欄舊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