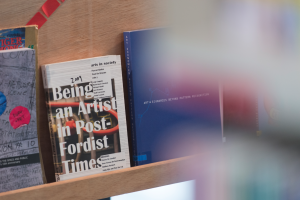藝術系統內部環環緊扣。藝術家、策展人、藝術行政、畫廊,各佔一席,難言直接單向的僱傭關係。正在書寫創意勞工(creative labour)議題的何建宗說到,全球資本流動讓工作性質碎片化,大家也以自僱性質(freelance)工作,形成不同的工作關係,「也自然讓剝削方式轉變了,存在互相剝削的成分。因為大家也盤算着自身的事業。」他提到,當年輕藝術家置身不同的結構,欠缺話語權,會以「自我剝削」(例如無償工作)來換取文化資本,讓剝削愈漸合理化。
當流動資本糅雜本地文化產業,便成了另一種勞動景象。梁寶山直言,西九所標誌的「大型文化藝術區」硬件,以至隨之而來的保育與活化等政策,成為「個體戶」藝術家面臨轉變的重要背景。「全球的工作也正出現”Ethno-lingustic division of labour”(語言族羣的分工),包括藝術圈。許多畫廊的高層也是能操流利英語、未必成長於香港的外國精英。西九的高層位置同樣是全球招聘。整個商業藝術圈也並沒有關顧本地的藝術勞工。但他們也需要一些了解本地環境的員工在現場執行,做些實務工作。 」因此我們不難觀察到,即使政府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仍是汰弱留強,未能惠及本地藝術勞工。
工會是潤滑劑
梁寶山既是藝術家,同時長期研究藝術勞動議題,早年已積極爭取藝術家的權益。問及工會能否改善藝術家的處境?她直道:「工會是資本主義的潤滑劑。」她解釋道,工會事實上在資本主義運行不順時提供協助(如僱資糾紛),讓其能順利操作。因此需要細心思考工會的定位與效用。她談到工會的對象,以至參與的人數能否成為有效力的組織。「像美國編劇家工會,參加工會是入行的必要條件,這樣便能清晰定義“profession boundary”。」工會除了互通消息外,能否設立退休保障,或為產業政策倡議法例。這些亦是工會能擴展我們對藝術勞動的思考。
藝術圈內對工會的意見不一,「工會必然涉及集體談判權,若藝術家是『我只代表自己』,那必然產生矛盾。另一方面,香港的藝術家並不傾向想像自己為勞工。」梁寶山說到, 好像Richard Florida便曾提出“CreativeClass”,浪漫化勞動想像。所謂藝術的自主是否仍深陷於當前資本主義的勞動結構,以疑幻疑真的自由來延續?
後記:Free Artists
在藝術產業裏,深埋許多隱性勞動:藝術行政、教育、保安,與藝術家成了相連的角色。他們的勞動狀態不一,卻幾近面對同樣不穩定與欠缺保障的工作特性。當藝術家同時身任零碎的藝術崗位,藝術家工會,又能否保障更多不同的藝術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