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和他們密不可分的人,某天突然離去,於是,心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洞。家福和美沙紀分別把蜷縮在自己的心洞裏。
這是創傷的一種。
電影《Drive My Car》就是關於這樣的一種創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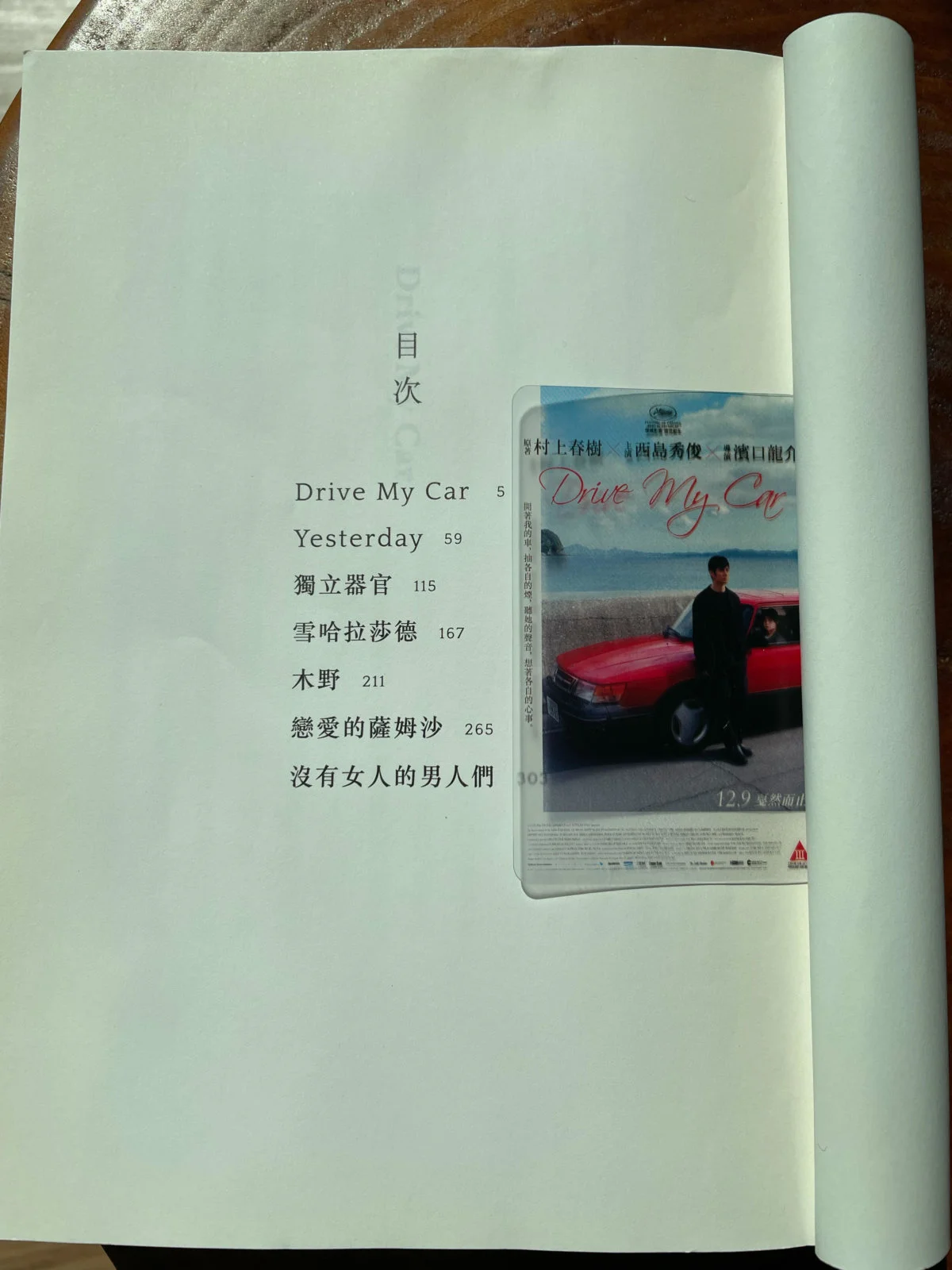
文學改編成電影之難,或許在於觀眾的期待。人們總是期望在電影中看到導演演繹出自己對於原著的讀法,有時候就像,觀看導演被原著綑縛着跳舞。可是,改編其實是一種建基於原著的重新創造。
與其說,濱口龍介改編了村上春樹的小說,不如說,他重新建構出村上筆下的創傷世界,加以延伸,再摻進了自己的意念和想像。
因此,電影中的家福,並不全然是小說《Drive My Car》中的家福,而是揉合了村上春樹筆下一眾被妻子的出軌及出走所傷害的男人翁特質,所形成的新的角色。這個家福,既是〈木野〉裏,因一次到外地公幹提早回家而撞破妻子和情人幽會的木野;也是〈雪哈拉莎德〉每次裏跟雪哈拉莎德發生關後在牀上傾聽她說故事的羽原;同時是《刺殺騎士兵團》裏被妻子所遺棄,為了治療感情傷口而一直駕車到遠方旅行的畫家。
尋妻一直是村上春樹小說其中一個重要而常用的情節。 一個男人失去了妻子,在心理上就是跟自己陰性的面向出現了不協調、矛盾以至衝突。因此,尋妻也是尋回在不自覺的時候失落了的自己的碎片,再拼湊出新的面貌。不過,《Drive My Car》的主題也關於死亡。在電影中,妻子的逝去,帶給家福的空虛感,不止於,這個人在物質世界死了,因此她在他的精神上更顯得無處不在,更在於,關係表面上的密不可分,早已被妻子感情上的背叛戳穿,家福無法止息疑惑,究竟真正的妻子,是日常生活裏那個熟悉的人,還是跟其他男人在一起,他看不到的另一面?人究竟只有一個真正的面貌,還是眾多假面也織出了更富層次感的真面目?
電影裏的家福,在妻子死後,開車到瀨戶內海,參與一項工作。他在車子裏一邊聽着亡妻留下來的記錄了妻子聲音的卡式帶,一邊唸着舞台劇台詞,就像二人仍然在對話。紅色的車子像一個鮮豔而淌血的心,也像一個繭,他把自己包覆在內。直至沉默而無表情的年輕女孩美沙紀當上了他的司機,握着他的方向盤,成為了他的聽眾、觀眾,甚至讓他不自覺地聯想到,早已在四歲那年死去的女兒。「如果女兒順利長大,她現在跟你一樣是廿三歲。」他對美沙紀這樣說。美沙紀也在想,如果家福是自己的父親(而不是那個早已離家出走的人),她希望他對自己說什麼?失去了的人,再也無法重回自己的生命裏,可是,逝者的幻影不斷召喚不同的人,來到他們身旁,成為一個扮演者,投影出他們深藏的強烈情緒。
美沙紀對家福說:「我殺死了母親,因為房子塌下時,我獨自逃山來,明明知道她仍在瓦礫下,卻沒法叫人來救她。」
家福對美沙紀說:「我殺死了妻子。她說那夜有話跟我說,我卻在外面蹓躂到很晚才回家,回去時她已死去。」
翻開死亡之傷,那些膿包和血污,全是因太深的愛而帶來的憤恨、內疚、遺憾、失落和痛苦,無路可逃,無可推諉,回力鏢於是又回到自己身上。
家福和美沙紀遇到對方,扮演了某個不再回來的人,於是,他們經過了對方,走出自己的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