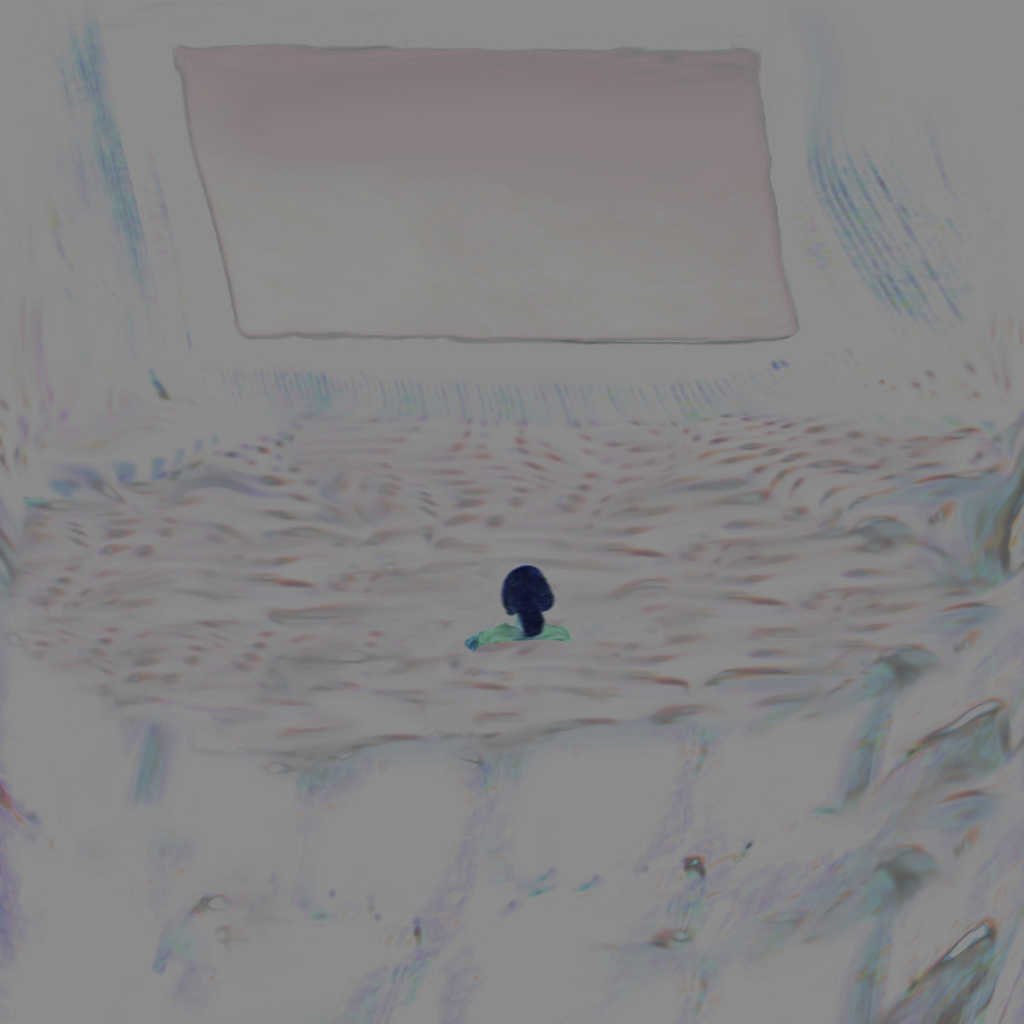
有些人因為渴望找到合適的電影,於是閱讀影評。影評有其功能性的一面,但它卻不永遠只是附庸角色,有某一類型的影評,它能讓你投入文字的世界,甚至你會希望以「文學」來形容它──它不再只是評論,而是有其深度及閱讀的愉悅。資深的影評人及學者黃愛玲早前離世,不少人再次談到影評的文學性這議題。到底什麼是影評中的文學性呢?我們找來幾位多年持續書寫的影評人及讀者,談談影評這文體的文學可能。
影評的定義是什麼?影評人及作家朗天認為,電影評論是一種以客觀、有理據地對電影作出判斷、分析的文體,而且必須有例證來支持評論中提出的觀點,他為電影評論下了這樣的定義,門檻絕對不低。而事實上,很多影評也未必能符合這個定義,很多時,人們只關心電影是否好看,影評人打了幾多「星」,朗天說影評不應只是消費指南,更應該帶給讀者乃至觀者新的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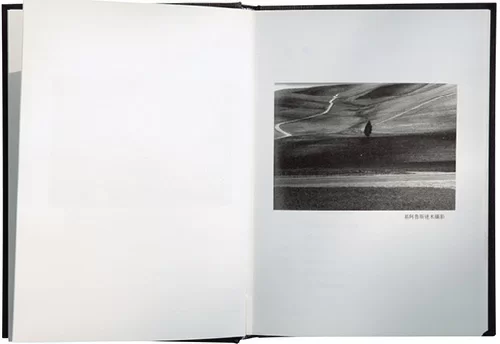
然而,電影評論又能否成為文學?如果我們理解電影評論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文章,評論會否缺乏了美感而喪失了成為文學的可能?朗天則坦言,文學需要有一定的美感,但電影評論也不至於用論文格式來寫,「例如蒙田的隨筆,到底是散文還是論文?他的作品優美,但內裏亦包含理據,是評論也是隨筆。」評論與美感交織的文字,往往令人陶醉其中,有時甚至會迷失,到底在讀的是散文隨筆,抑或是有縝密論據的評論文章,撲朔迷離。而黃愛玲的文章,就是帶人進入了這種狀態,「她的文字令人愉悅,同時論影,她以文字跟讀者結緣,作者跟電影、讀者跟作者,她的文字成為了橋樑。」朗天這樣說。
無用的滲透
有類似想法的,還有電影研究學者羅展鳳。「有許多電影,我都是因為愛玲的文字,我才再去觀看,然後認識。」羅展鳳認為,影評與文學之間沒有必然性,但如果作者在影評中加進文學的成分,許多時卻能讓讀者為之着迷,「有時我會想到,愛玲的文字,其實是文如其人的。她當然是對電影有一種熱愛,但她本人的氣質,卻能在影評中展露出來,那是誠實的。」
所謂誠實,是將觀影的感受如實地書寫出來,就算是負面的看法,也如實地呈現出來,「例如她寫關於《大逃殺》的影評,她也可以說深作欣二晚節不保!」
對羅展鳳而言,所謂文學性,不局限於文學的技巧,而是在於作者如何用文字,與讀者產生聯繫,「有時影評人寫的,其實是他自己的感受。他到底從電影中,聯繫到怎樣的個人經歷呢?在這種寫作中,評論與散文的界限其實是很難區分的。」
於是看似功用性的評論,就有機會被文學那彷彿是「無用」的性質滲入,也許那不是最有分析性最有洞見的評論文章,卻有了「文學」那無用之用。「我不會覺得文學是無用的,而有文學性的影評也自然不會是無用,當文字能讓人可以投入那電影,甚至分享到作者個人的體驗,那麼有文學性的影評,其實是可以影響到一個人的行為,那也是藝術的功用。」羅展鳳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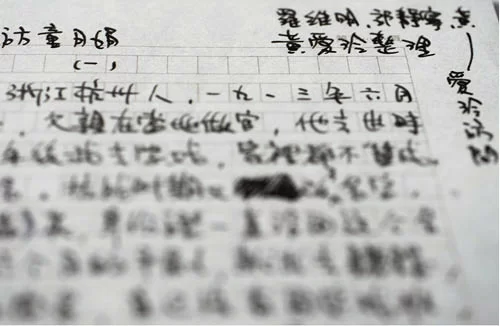
影評多樣性
黃愛玲的文字就如紅娘,風韻、美麗,卻不是主角,讀者透過她的文字認識電影,與電影結緣,但有時候,她的文字過分迷人,讀着,竟無法抽離,影評文字本來是線,卻竟成為「緣」之本身,「就是景、物相融,是通過她的文字去認識電影,抑或是與她的文字結緣,邊界已模糊了。」朗天這樣說,「雖然文字有美感,但內裏依然有理據憑證的,卻不會展開,展開了就煞風景了。當你分不清誰是紅娘誰是崔鶯鶯時,或者你兩個同樣愛?」
朗天的影評與黃愛玲南轅北轍,不是為了與人結緣,而是為了刺激讀者,「讀者被文字喚醒,啟發他們,然後他們會生出自己的想法。我認為電影評論應該是有創造性的,要有創新的觀點!要有衝擊,讓人耳目一新。」對於他來說,影評人就如藝術家,要不斷創新,而影評也跟藝術品一樣,能夠刺激人的精神活動,在這層意義上,文學、電影評論與藝術,也許該是殊途同歸。
而羅展鳳則認為,影評不只得一種,「就算我自己關於電影的寫作來說,也不只限於一種寫法的。可以是比較研究性質,同時也可以有較抒情的寫法。」她也認為,在影評這文類中,需要有不同的書寫方式,可以是有創新觀點、有理論的,也可以是用文學角度去介入,重要的其實是影評的多樣性。
上世紀影評

電影與文學總是互相影響,又互相吸引,而影評則總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好多電影本身同文學有關,但影評不一定是文學作品。」資深影評人石琪開宗明義說道,「影評不一定具有文學性,要視乎由誰來寫。」他把上世紀文人寫影評的盛況娓娓道來。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社會生活並不富裕,主要娛樂就是看電影,電影不單只是大眾娛樂,還是吸收知識的渠道,報章、雜誌的影評專欄大行其道,深受讀者重視。另一邊廂,文人生活拮据,要賺錢就要多寫文章,「尤其是在報社工作的,又做記者又做編輯,都不夠錢用,甚至還要寫波經、馬經。」他指出許多後來為人所知的文學家,早年也有涉足影評。
「金庸是電影發燒友,他早期在左派報紙如《大公報》、《新晚報》上寫影評,他又有編電影雜誌,長城電影公司出版的《長城畫報》介紹世界各地的著名電影。」在查良鏞以「金庸」筆名寫武俠小說成名之前,上世紀五十年代,他便曾以「林歡」為名寫影評,光在《長城畫報》,就至少發表了五十篇關於電影評論、理論、製作等,內容非常多元化。「這些文人所寫的影評,其文學性不一定在於文字上,而在於作者非常熟悉中外文學作品,許多電影正是由文學作品改編,如《紅樓夢》、《戰爭與和平》等,他們通過原著來介紹電影,影評的文學性也因而提升。」而詩人所寫的影評,則富有感染力。「崑南本身是詩人、小說家,他的文筆才氣洋溢,金炳興也一樣,詩人寫文章有一種霸氣,詩人是天生寫字的人,無論他們的觀點如何,總之一寫出來,就非常有感染力。」
將電影改成文字

1952年出版的《中國學生周報》,可謂本地影評書寫的里程碑,匯集了大量的文藝青年及電影發燒友,「西西和亦舒最初也有幫《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寫,訪問明星、寫電影評論。」石琪形容西西「很迷電影」,由1970年起在《快報》寫的專欄《我之試寫室》,當中便包括電影評論和隨筆。那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年代,五湖四海的作家,帶來了各式各樣的影評。
嶺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淑嫻則認為,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影評因電影改編文學作品甚多,對影評人的文學造詣有較高的要求,然而到了今天,當電影改編作品相對較少,影評中的文學性卻仍有其存在意義。「影評的文學性,在幾個層面上可以產生作用。其中一點是在人物描述之上,文學的寫法可以將電影中的角色描繪得更活靈活現。例如黃愛玲在寫《苦命鴛鴦》的影評時,形容『李香琴的壞是漂白水也洗刷不了的壞』,那不是電影中原有的,而是影評人的感受。」
這其實就是第二種意義的「文學改編」,不同於由文學作品改為電影,影評可以將任何電影作品,「改編」成文字的模式,文學就是一種手法,讓影評得以得到潤飾。「畢竟影評的載體是文字,它不同電影般同時利用不同的範疇如影像、音樂,所以當想用文字評論電影時,必然需要有所轉化,甚至利用文字的想像力。文學有時就有這功用,有時它甚至可以補充電影所沒有的東西。混合了理性的觀察,結合個人的想像,好像黃愛玲所寫的,『看到《小兒女》裡王萊和王引偷得浮生半日閒,在家門前的院子喝下午茶,小圓桌上鋪了格仔檯布,就主觀地將黑白菲林的深灰變成萬里無雲的蔚藍;生活可以謙卑而優雅』,這種聯想力,甚至有時帶來的電影感,其實就是文學的力量。」黃淑嫻這樣說。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