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每個醫生都用心,也不是每個病人都聽話。我用了二十多年時間,走了很多彎路,才學懂如何看醫生!病人也有責任,只要一個人學會了面對,就算爬着前行,也是有一點進步的。」紮着馬尾的May眼神明亮活躍,在活潑的表情之下,很難想像過去二十六年來她所經受的種種精神折磨,如何吞噬着自我──在不同階段,她被診斷過有抑鬱症、焦慮症、精神分裂症和躁鬱症。

十八歲那年,May在大學預科考場上感到頭昏腦脹。「我覺得有個七、八歲的男孩在旁邊,時不時逗我玩。」那時候搭的士,她會覺得珠簾坐墊上有千萬雙眼珠,街上路人盡是全身佈滿眼睛的「眼人」。在家裏,她一看到婆婆抽煙就覺得有蛇纏到手上,洗菜的塑膠筲箕有血紋在流淌。
「家人叫我吃冬菇,看起來卻是屎塔!他們說吃節瓜,我覺得是嬰兒肉!拿起一個碗,景泰藍的顏色都像有毒滲出來!叫我怎麼吃得下!」世界變得很陌生,處處是荒誕。May述說這段記憶時,不禁雙眉緊蹙。
May的異常體驗令家人一時束手無策,父母於是花了5,000元請來一位道士為她作法驅邪。5,000元在八十年代末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她只記得作法時又吵又混雜,把她嚇得哆嗦躲在檯底。
這道士當然沒有治好她,伴隨而來的是她人生第一場打擊──讀不到大學了。只好出來做事,但份份工都做不長,「總覺得同事對自己不好」。「得了一種不能對人說的病,沒有朋友,無社交活動。每天情緒很低落,傾向毀滅自己,病了之後不再照相,甚至扔掉所有自己與親人的照片。」
那時母親帶她去吃齋宴,茶樓的吵鬧聲令她驚恐萬分。「我覺得周圍幾張吃東西的人都是我的喉舌,眾人吃的東西都入我的身體。」
第二次病發
那年代,精神病是個很大的禁忌,社會大眾對此亦缺乏認識。母親第一次帶她去看私人執業精神科醫生,看完依然一頭霧水。接着又看第二個,醫生說她只是「扭計」。「那時真的不懂看醫生,完全不知道為何要看,也不知道見醫生做了什麼。因為不懂得表達,走了很多冤枉路。」May發出了幾聲嘆息。
她看得最長時間的那位醫生,最初診斷她情緒紊亂,之後又改為抑鬱症。醫治了四年後,家人覺得「應該已經醫好了」,於是私底下減藥,她很快就第二次病發了。
這次病情來得更加兇猛,思路更加混亂。她有時覺得自己是個貨櫃,別人正往自己身上刷油漆,還有毒蛇鑽入了手臂……「那些應該是幻覺」。出街時,她感到毛骨悚然,覺得周遭都是不同層數的地獄,在車裏駕車的司機都是紙紮公仔……去醫生診所,翻開雜誌見到書頁上有隻狗,「原來那隻狗就是我,醫生是玉皇大帝要審判我……」她的生活被一個個驚慄的片段塞滿。「當時完全不知這是病徵。」
那時量血壓、度體重之後,醫生問,「睡得嗎?」「吃得嗎?」有時還一邊問診一邊看錶。May安慰自己:「反正看得愈久收費愈高,我也少點說話,以免愈久愈貴。」這樣一醫就是七、八年。
生死邊緣
1996年,她試過看心理輔導,四十五分鐘收費800元。輔導員說:「其實沒什麼幫到你,只是做你的朋友。」她辛苦工作存得的錢都花來治療了。直到用完自己的積蓄就斷了輔導。

第三次復發時,原本的醫生放大假,換了個新醫生,因用藥過重,她的頭都歪了,打了解針才漸漸好起來。
「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你知道多困擾嗎?」有次她穿粉紅色衣服走向巴士站,「聽到」周圍素不相識的人都嘲笑她:「粉紅衣粉紅袋,像新娘。」
「當時很驚,壓力很大。」走入商場,又覺得四周的人在說:「隨便上一架的士,都會送你入醫院!」
第四次復發,她轉到公立醫院治療。病了多年,入院近十次,而且愈來愈密,愈住愈久,幾乎每四年復發一次,似乎置身於無底洞,十分絕望。
「沒得醫,一出院就想自殺。」她試過站在二十八樓露台,伸出腳幸好被人拉回來。試過要跳山,誰知原本空寂無人的山頭突然來了一個伯伯,一直不肯走。「最後我說你不走,我走!」如今說起那生死邊緣,她的語氣倒有幾分輕鬆。
互信帶來轉機
2007年,九龍醫院為她做了心理治療。她最記得醫生分析了尋死的好處和壞處。「問題沒解決,像銀行轉帳一樣,這筆帳轉入別人的帳戶了,讓他人來解決而已。」她猛然想起:「目前起碼還給一點家用媽媽。如果死了,媽媽連2,000元都沒有了……」這個想法令她暫時打消尋死念頭。
談起最近的一次復發,全家瘦了十磅。「真的很驚!」May迅速將雙手交錯抱胸,「看電視會覺得電視劇內容都是商討怎麼樣整死我,還有記者跟蹤偷拍。」她入院時到醫生面前猛叩頭,央求護士不要殺她。
「我第一次被五花大綁,姑娘其實是在救我,幫助我穩定情緒,以免我磕到頭崩。」她摸摸前額頭,有一塊地方毛髮不生。那時護士扯住她頭髮,阻止她撞到頭破血流。
2009年3月,May出院時被轉介給個案經理長期跟進。正因為與醫護之間的密切互動,為治療帶來轉機。「社康姑娘跟了我幾年,建立了互信。例如什麼時候減藥、新藥舊藥差別,信息量充足。我記得姑娘和我說過『萬事有商量,我會與你一起找解決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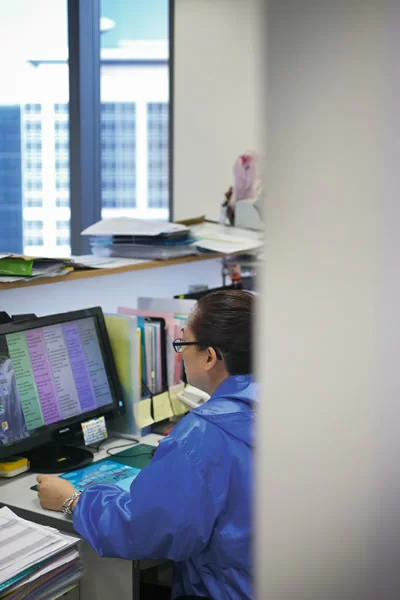
久病成醫
現在,May每半年驗一次血,檢查是否重金屬超標。她每天要吃五種藥,三種穩定情緒、一種解藥,以及輕微小量的心臟藥以解手震。服藥後最明顯的副作用就是肥了三十磅!「胃口很好,但動作遲鈍。」她最近才無緣無故摔了一跤,走起路還有點失衡。
訪問期間,她不停地喝水。「不好意思,藥有副作用,會有口氣。」為了保持口腔清潔,她不停吃香口膠,一天刷三次牙。
「以前不懂得愛護自己,不了解病情,更不懂得向醫生彙報。」久病成醫的她深知醫生時間有限,覆診前會先做好筆記,一見到醫生時逐項核對。「一旦漏說,出了醫生房就很麻煩。我轉數不夠醫生快,要做好準備。準備充足了,有時只需要五、六分鐘就已經交談了很多事,還包括說bye bye。」
最令她開心是醫生信任她「搞得掂」,還稱讚她「成為自己的治療師。」她笑起來眼睛瞇成彎彎的月牙。
「為何別人給東西總覺得像屎塔,因為自己不喜歡卻要硬着頭皮接受,過多的被迫順從外界環境,自我會被壓抑。為何覺得到處都有千萬雙眼睛?因為害怕他人的目光和評價。而見到血其實是壓力太大,蛇也是源於一種內心的憤怒……」當她勇於將內心的芒刺一根根拔出,心靈開始成長。
父親至今無法接受她生病
「其實我自小倔強,不服從父母的強權。看父母打罵兄弟姊妹,覺得讀書成績好便是生存伎倆。自小父親就灌輸『俾心機讀書』,長大別像他一樣做粗工。但不懂得處理考大學這樣的壓力事件。」
十八歲的她想和媽媽談,卻見阿媽每日辛苦操勞,看電視成為每日最開心的時間,於是欲言又止。解決不到的問題,迫着自己想辦法。同樣,在工作中不懂得說不,排山倒海的工作量令她壓力爆煲。「我以為勤力就賺到錢,其實世界不是這樣的,人際關係、際遇、健康都是方方面面的綜合影響一個人的成就!
「很多人不敢去看病,因為擔心被歧視。我當初很怕親友指指點點,有種『唔衰得』的心態。可是,諱疾忌醫會延誤診治。其實精神病人不舒服已經很慘了,外人為何還要批評呢?」May不敢上鏡,因為父親至今無法接受她患病。父親原本最疼愛她,愛之深痛之切。多得母親一路扶持,同走這條崎嶇路。
她語重心長地說:「最無助莫過於甘於無助,只要不放棄自己,努力適應生活,做不到成功的人,起碼可以努力做普通人。活着一天,就有一天的機會。」
May在推動精神健康的NGO利民會工作了八年,更成為家中的經濟支柱。「我做人這麼久,什麼時候是最好的?就是現在!」
文章選自《明周》2410期封面故事《精神病患 復元崎嶇路》。
本專題獲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 「2016年度卓越新聞獎」之「榮譽卓越專題特寫獎」(Honorable M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