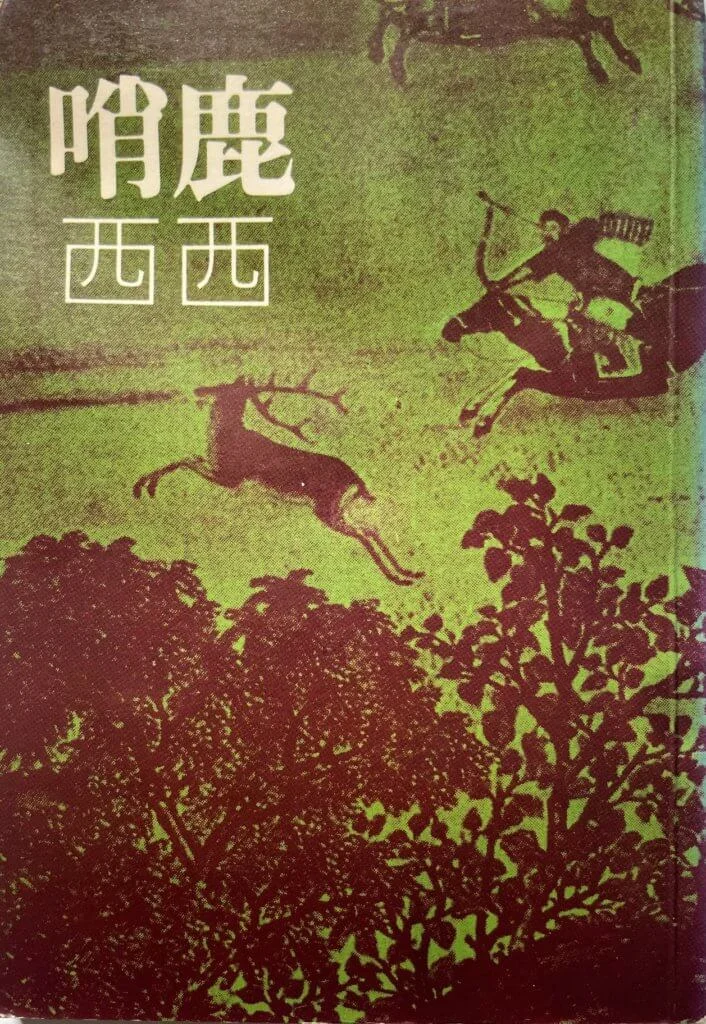西西的最後力作《欽天監》是一部歷史小說,也是西西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所滿意之處,是創新,是從來沒有人這樣寫。不止是說,沒有人這樣寫有關康熙的歷史題材,更是指,沒有人這樣寫「歷史小說」,甚至是,沒有人這樣「寫小說」。
用小說形式處理歷史題材,西西早就有所探索。短篇如《浮城誌異》,長篇如《飛氈》,都是以香港歷史為書寫對象,而八十年代初的《哨鹿》,更是同樣以清朝歷史為底本。但只要深入閱讀便會發現,西西的終極視界,並不止於香港史和中國史的範圍,甚至超出了世界史,而進入自然史的層次。在《欽天監》接近尾聲,蒙古青年阿克伊說:「天是沒有國界的,沒有國族,星斗滿天,叫星宿,可不是叫星族。」短短數語,可圈可點。
不過,落實為特定時空,小說的焦點還是在康熙年間的歷史。所以籠統地稱為歷史小說並沒有錯。只是,西西的創新之所在,亦同時是對歷史小說這個類型的抗衡,以掙脫箇中的約束,達至書寫的自由。《欽天監》不以真實歷史人物為主角,沒有戲劇化的主線故事,亦不追求寫實擬真的效果。換句話說,西西拒絕營造歷史「本然如此」的假象。相反,她通過虛構的敘事者(欽天監學生閎兒)的眼光,去旁觀歷史發展,重構歷史經驗,並對歷史作出評價。據西西的說法,就是在事實上「有所本」,而想像卻「沒有限定」。
一般人對於歷史的認知,就是事實上已經發生的事,所以寫作歷史小說的時候,必然會出現是否「忠於歷史」的考慮。在日本明治至大正時期,晚年以歷史小說著稱的森鷗外,便已經探討過這個問題,說穿了不外乎是「遵從歷史」和「脫離歷史」兩種取向。事實上,完全遵從和完全脫離歷史,也同樣不可能。歷史原本的模樣已不可復現,能遵從或忠於的,只是留傳下來的史料或記載。相反如果完全虛構,也就談不上歷史。所以歷史小說永遠是在兩者之間遊移,這本身並不是什麼秘密。但一般的歷史小說,把這個內在矛盾和予以消解的過程隱藏起來,當作就是原本的事情一樣,以自然主義的方式向讀者呈現。當年森鷗外要抵抗的,就是這種歷史小說。我認為西西在《欽天監》中所做的,也是這樣的事,只是方式和鷗外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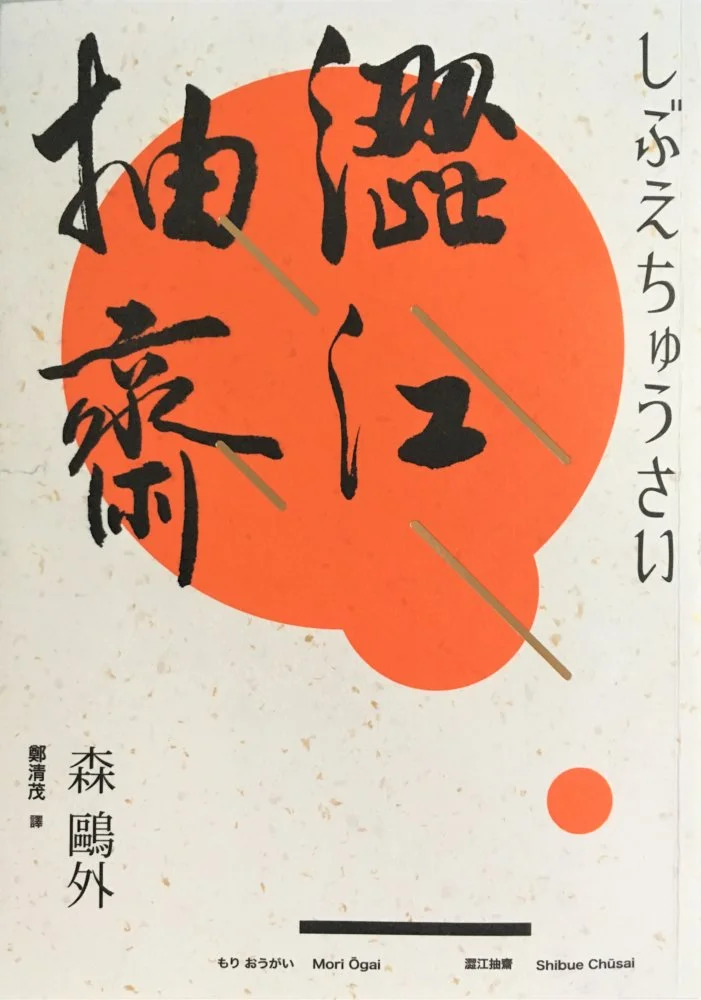
康熙時期的歷史,一方面是清朝的輝煌盛世,另一方面也充滿開國之初對異己的防備和壓制,以及專制王朝所不免的權力鬥爭。這些都是極富戲劇性的小說題材,但西西偏偏不去直寫,而採用了經過有限敘事者的旁觀角度的側寫。閎兒在小說的大半篇幅中,處於從童年到青年的成長階段。他以欽天監學生的身份,從老師和前輩口中得知當朝和前朝的史事。關於這些歷史大事,他多半沒有第一手經驗。他先是一個聆聽者、收納者、消化者,然後才是一個講述者、傳播者和評論者。他把學習和聽聞的事情,轉告青梅竹馬的女伴容兒(後來成為他的妻子)。兩人的對話(以閎兒的講述為主,容兒間中回應)成為了小說的本體,也成為了作者西西向讀者講話的「傳聲筒」。
閎兒是個天真單純,品性善良,充滿好奇心的人。加上他的學生角色,令他的敘述流露出典型的西西式童真語調。當然在小說的後半,他已經成長,增長了識見和閱歷,當上了欽天監的天文官,已非當初的無知小兒,但小說的基調並沒有明顯的變化。連他的兩位一起在欽天監裏長大的同學寧兒和阿克伊,人到中年,官至中品,還是保持着當初樸實清純的品性,率直而沒有機心。可以說,人如其文,這是西西本人的一種反映,就算那是虛構小說。
沒錯,《欽天監》的題材是沉重的。書中傳遞的天文學知識雖然趣味盎然,種種古代文化、文藝、文物介紹也令人神往,但背景卻是專制王朝對自由精神的壓抑,以及「一人的自由」(黑格爾語,指皇帝)和平民百姓的奴役的扭曲結構。就算是居中的達官要人也無可作為,甚至自身難保。到了最後,康熙駕崩,雍正繼位,前朝寵臣趙昌被抄家。提早退隱的周若閎接受趙大哥託孤,為孩子改名天佑,為更是全書悲情的頂點。但這至為黑暗的一筆,卻不見用力着墨。
這絕對不是疏忽或閃失。西西最出人意表之處是以輕寫重。早期的《哨鹿》已嫻熟於節制的藝術,但情緒顏色還是比較濃重。來到最後的《欽天監》,才真正的展現出何謂舉重若輕。說到西西的「輕」,是指她的筆法,而非題材或見地。從純真的人物口中,以純真的語氣講述,並不代表沒有洞見和深刻的感受。一般以為歷史的批判和喟嘆,必以重筆出之。西西卻以輕描淡寫的手法,留下了無法言詮的弦外之音。
卡爾維諾在《給下一個千年的備忘錄》 中列舉的文學特質配對,輕和重是其中一組,而兩者必然是互為表裏的。沒有重就不成輕,沒有輕也不成重。重視輕,不代表忽視重;反之亦然。說西西的輕盈,並非不明或不知她的厚重;說西西的趣味,也非不明或不知她的認真。輕與重,樂與悲,遊戲與嚴謹,誰都知道是雙面的。就正如把香港百年歷史寄放於一張輕盈的飛氈,人類歷史的沉積,亦如細若微塵的繁星,懸浮在無重的太空中,投映至薄紙之上,以點點的墨跡摹描。西西以《欽天監》為我們創造出新的雙重意象──抬頭是天,腳下是地,輕和重,自由與安穩,構成了人生的兩難,歷史的迷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