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法律的議會,是一個政治機關。執行法律的法院,是一個司法機構,法官只負責解釋法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認為,在今日的香港,只要不是牽涉政治的案件,香港的司法依然行之有效,然而,真正的公義,是建基於公民的政治理想判斷,法律不能解決政治問題。一個法治社會,應當跟政治有距離。

作為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在風高浪急之時,依然願意接受傳媒訪問。擔任院長已經一年,辦公室從六樓層搬到十樓。「為什麼市民以前從來不會抱怨私人檢控出現問題?」傅華伶教授反問記者。「大家心裏都明白,這不是一個法律能夠解決的問題,這是政治問題。」立法、議會、選舉、街頭抗爭,他逐一羅列,無一不是政治問題。「只是現在好像沒有其他的路可行,唯有拿法律出氣。
「法律許多時都是解決例外的問題。」傅華伶舉例,例如殺人、販毒、偷竊。「為什麼一般人不會偷竊?大家的答案肯定是—從來沒有想過要偷竊。為什麼沒有想過呢?因為從小到大,社會教育認為偷竊是一件壞事。」假如一個人因為擔心受刑罰而不敢偷竊,這個人其實是有問題。
⚡ 文章目錄
認識政府的權與責
面對龐大的司法架構,平民百姓往往望之生畏。
現代國家的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國家(政府)是宣稱能夠合法使用暴力(武力)的機構—這是韋伯觀察所得的結論,他是德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及哲學家。「暴力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傅華伶解釋,由執法、檢控到判刑,每一環都是一種「暴力」,例如判刑就可以剝奪一個人的自由。「現代國家不容許其他人擁有使用暴力的權利,就算是國家首富,也不可能興建一個私人監獄,或者建立一個私人軍隊。」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Jeremy Waldron曾於二〇〇八年撰寫〈The Concept and The Rule of Law〉一文,指出法律條文與裁決都必須是公開,以及建基於理性,公民能夠理解法律的邏輯與理據,從而實行理性的自治。按此邏輯推論,一旦國家的立法與執法不再尊重公民作為理性而自主的個體,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法治。
無論是市民還是政府,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解釋:「所有人都必須服從法律,無人可凌駕於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論身份地位高低、不管是公共機構或一般市民,均受法律約束,並須承擔法律責任。」換言之,即使是政府,也需要按法律行使權力,政府的行為是受到法律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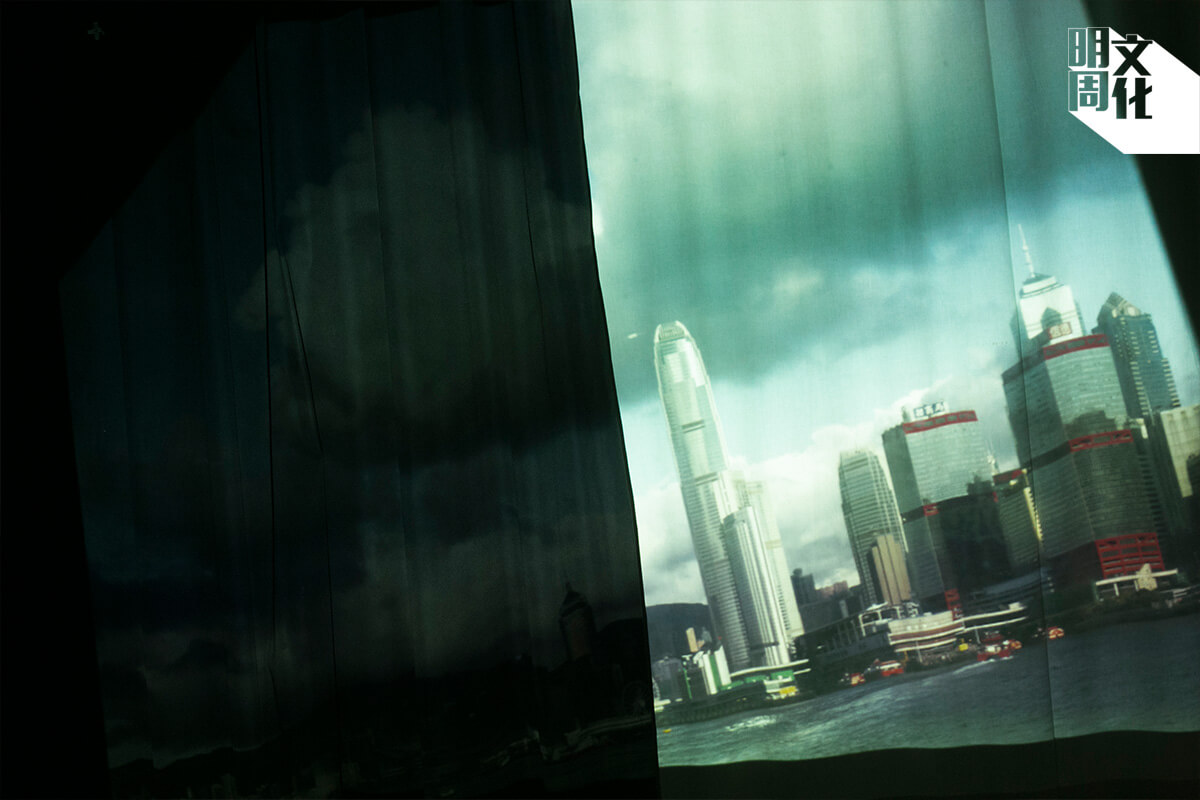
法律如何規範政府行為?翻開《基本法》,第二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第六十四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 」
一個市民違法,執法機關需要先調查,找到切實及可信的證據,才可以拘捕事主。律政司會向政府各個部門提供法律指引,決定是否提出檢控。在香港,刑事檢控工作由律政司司長全權負責。簡易層次的檢控工作,會由警方或其他調查機關處理,在裁判法院經由高級法庭檢控主任代律政司司長審閱。
「如果任何一個國家的警察和法院都是腐敗的,法律就會變得不理智,充滿偏見和歧視,這個社會就不可能有法治。」傅華伶說。
為什麼市民會認為判決不公?
基於上述的法律概念,假如一個市民的自身權益受損,理應能夠透過司法程序尋求公義。傅華伶認為,只要不是牽涉政治的案件,香港的司法依然行之有效。「問題是,真正的公義,是建基於公民的政治理想判斷。」香港目前的狀態較為分化,政治問題永遠是五五開或是六四比。無論法官作出什麼判決,一定會有一半人拍手,一半人跳腳。「這是一個法官永遠無法承擔的責任,大家將這個責任放到法官肩上,其實非常不公平。」 他說。
牽涉政治的案件,最近期就是有關反送中運動的案件。社會各方,包括旁聽的市民,都曾對法官的判決表示不滿。一個人怎樣可以當法官?讀完法學院執業,可能比一般人聰明,大家覺得這個律師不錯,經同儕推薦,由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再由行政長官按推薦任命。「法官沒有經歷選舉,也沒有社會的認同,不認識多少政治,為什麼會由法官解決這麼大的憲法問題?政治問題,用法律解決,法律就很難為了。」
說起反送中運動,傅華伶先向記者核實最新的統計數字:「現在因為反送中運動被拘捕的人,過萬人了沒有?」根據警方於二〇二〇年九月六日的統計,已有10,016人被拘捕,2210人被檢控。根據懲教署統計,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為止,共有6859名在囚人士,其中4880個是本地人。「這一萬人當中,我估計至少有一半是年輕人。這麼多年輕人,在一年時間,前所未有地違法了。違法的人不再是例外,足以說明社會在根本上出了問題。」

傅華伶用最簡單的數學計算,假設每個人都是來自一個四人家庭,受影響的人就有四萬人;假設每個人都有四個朋友,就是八萬人……一直算下去,就是一個極龐大的羣體。「他們的訴求,警方執法的問題,法官的判決也不能夠解決,最終一定是要通過某種政治過程,也就是一個政府的責任。
「法律不能解決政治問題。」傅華伶再次強調。他認為,香港社會的政治狀況未能得到大眾的足夠信任,所以社會高度依賴法律,賦予法官一個本來沒有的地位,然後想像法律能夠起到一些不能起到的作用,最後決定對法律失望。他指出,制定法律的議會,是一個政治機關。執行法律的法院,是一個司法機構,法官只負責解釋法律。「如果法律能夠解決政治問題,法律本身就出問題了。」
打官司不止是講法律
要解決香港的政治問題,就不得不回到《基本法》。有人或許會疑惑:我只是一個小市民,打官司不就是講法律,談什麼政治?
事實上,一個市民要提控或者被檢控,一切都是與《基本法》有關:例如第二十五條列明「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又例如第二十八條列明「香港居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基本法》作為香港憲法,是在立法和行政之上,但是通過法院運作。
傅華伶指出,「當初設計《基本法》的時候,大家可能都知道《基本法》會出問題,在想像中以為有方法解決。或許是沒有解決好了,我們就上街了。中央怎麼辦?就是看看中國的憲法還有什麼可用。結果,雙方都走出了《基本法》的框架。」

今年七月一日,國安法通過後翌日,唐英傑涉嫌駕駛一輛插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撞向三名警員,成為國安法首個被告。傅華伶認為,唐英傑的案件,恐怕就是一個測試。「法官如何在執行國安法的時候,維持香港普通法的現狀,目前還是未知之數,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讓國安法對香港的影響愈少愈好。」
大家都不守法 法治就不存在
傅華伶專長中國憲法、法制、人權及大中華地區跨地域法律關係,他指出,「絕大多數的法律條文,其實都與政治沒有關係。」公司、上市、合同、結婚、離婚,常用的法律,大多是處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法官最大的作用是解決雙方的關係。」傅華伶說。
傅華伶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治社會的根基,就是大家都遵守法律。法律其實是一些大家願意共同遵守的原則,其合法性來自多數人接受,而不是由立法人員說了算。傅華伶打趣說,正如大多數人都不清楚合同法是如何寫,但是大家都願意遵守法律,是出自對制度有一定的信心。

最近有輿論認為應該設立「量刑委員會」,就所有刑事罪行發出具約束力的量刑標準。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於今年九月廿三日發表聲明回應:「量刑是一項司法職能,由法院獨立行使,是法院專有的職能……法庭的所有決定, 包括量刑決定,都是公開讓公眾討論的。」
馬道立亦於聲明內,引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於六月在立法會回應判刑問題所作的答覆:「法院的職責,是在被告人在個別案件中認罪或經審訊定罪後,因應案情和犯人的情況,應用相關的原則,判處公正而合適的刑罰。法庭會宣告判決理由。如被定罪的人認為刑罰過高,該人可提出上訴。如律政司司長認為判刑明顯過輕或過重,也可向上訴法庭申請覆核刑罰。
「經過一定的程序立法,大家就會願意遵守,是一種社會共識。」傅華伶說。一件事要送到法院處理,判決總是有分輸贏。「我們常說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其中一個表現就是敗訴一方就算不同意裁決,也會自動執行,同時再提出上訴。
「然而,假如大家對一個制度失去信任,法律也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假如大家都不守法,法治就不再存在。」傅華伶若有所感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