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屎埔村徑兩旁豎立了許多鐵絲網,村民盧永燊穿梭其中,與一名身穿制服的印巴籍保安擦肩而過,「恒基在這裏收購了八、九成土地,聘請他們日夜巡邏。」他見怪不怪,沿路與一些村民寒暄幾句,便走到村口的地政署告示板,仔細看看有沒有新通告,「發展商要起電纜或拆街燈,會經地政署在這裏張貼通告,諮詢期限一個月,錯過了就沒法提出反對,有時,這些通告會被人刻意遮掩,我要金睛火眼。」
從天而降的人為詛咒
地政署告示板的後方,是一個圍封了的大地盤,佔地約十七萬呎,「是恒基在這裏發展的第一幅地。」這地盤,動工比新界東北計劃的撥款、收地還要來得快。早在二〇一三年,政府將原定的「統一收地再招標」改為「公私營合作」模式運作,只要發展商儲存四萬呎以上相連土地,便可申請「原址換地」,改變農地土地用途,並能優先發展。
二〇一六年,恒基在馬屎埔進行平整工程申請「原址換地」,以石屎躉圍封十七萬呎地盤,結果堵塞了原有的天然水道,每遇打風落雨,地盤出現的積水猶如儲水池,隨後黃泥水沿主要通道湧出周邊農地,導致農地水浸、農作物報銷。繼後連續兩年的中秋節,挖泥機都破壞了食水管,村民無水過節,只能到馬適道旁的消防喉取用食水;近年,發展商興建地下停車場,導致村民平日灌溉的水井水位下降,影響農作物收成;每天從地盤傳出的鑽探聲和打樁聲,震耳欲聾,更讓村民難以忍受……
盧永燊是馬屎埔環境關注組核心成員,這幾年,他鍥而不捨地協助村民去信屋宇署和地政署,維護村民權益,「就是要讓政府知道,別以為強行動工就能夠一了百了。」他指,粉嶺北的第一階段收地,暫時只有兩戶收到遷離的確實期限;不過,工程一旦動工,各種滋擾會令村民更難以承受,到時政府收地就會更順利,「我們會繼續抗爭,不會放棄!二〇一四年,立法會議員兼財委會主席吳亮星在其他立法會未等議員埋位便進行投票,如果不是『反東北十三子』被捕引起關注,東北在二〇一七年已經清場。」
盧永燊的職業是自由身工作者,說話溫婉有條理,抗爭方式亦一如其人般斯文,每天巡村,與村民溝通,跟官方進行文件交涉,每一項工作都需要耐性和毅力,等同守護着村內的人與事。發現發展商偷偷拆去電纜,在地盤偷用消房喉,他會第一時間投訴;發現菜田連續多天失竊,他會大清早六點起牀,悄悄攝錄那些伸手入鐵絲網摘去農夫的矮瓜或生菜的人。追查之下,他發現那些小偷可以是一些晨運客,可以是附近私樓的住客,也可以是爬到樹上摘龍眼的工程人員。「他們辯稱,以為土地荒廢了,就可以隨意自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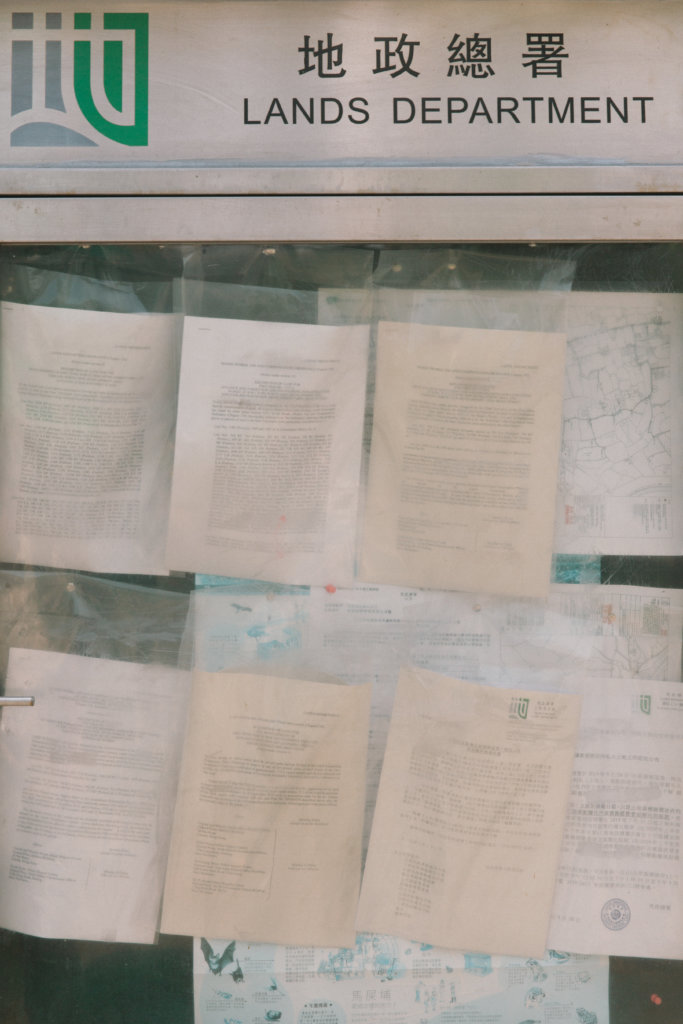
本來無戰線 何處惹抗爭
二〇一二年,盧永燊為了練習空竹(一種中國傳統雜技),那需要較大空間,便搬進馬屎埔。「來了之後,見識多了,了解到村民的生活節奏,知道什麼蔬菜什麼時候當造,每天看着蔬菜長大!」他自問曾是個「不問世事」的人,至二〇一六年,遇上一班前來馬屎埔聲援的抗爭者,大家在那塊十七萬呎土地上「守田」約兩個月,啟發他作為村民亦不能坐視不理,「他們跳上推土機,很大膽,我就幫手搬卡板,雖然大家互不相識,卻為着同一件事而努力。」
「撤田」之後,村民的抗爭戰線轉向不合作運動(拒絕接受任何賠償或安置),堅持不遷不拆原則;一些則對收地逆來順受—特別是年邁村民、忙於農務的農夫,沒能力消化複雜的賠償或安置細節,盧永燊便替他們做一些「懶人包」(其實是詳盡版之外加上親身講解),例如二〇一八年政府公布「510(賠償安置)方案」,表面看來賠償金額達一百二十萬,實質的賠償條件卻是居住的寮屋面積必須達一千平方呎,「大部分村民根本沒有千呎寮屋,其實,村民的家都只有四百平方呎左右,住上三十幾年,實際賠償只得四十八萬,何來會有一百二十萬呢?」為此,他協助馬屎埔陳伯(陳基裘)便就「510方案」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反對方案漠視寮屋價值,「每一個步驟都做好,對日後同樣面對發展的洪水橋、元朗南等寮屋居民也有幫助。」
去年,恒基入紙申請增加興建私樓的地積比率,他便到綠悠軒擺街站,收集意見和簽名,恒基申請最終不獲通過;又有一年,恒基向路政署申請拆村內街燈,他發起一人一信到民政署,還詳列四十一個反對理據(「拆燈後道路十分昏暗,路人容易摔倒」、「村落還有很多人居住,沒理由違反常理拆去路燈」),讓村民參考填寫,工程結果也被叫停。可惜的是,到了第二年,街燈仍被拆去。
「那些地政署的諮詢回條,意見欄只有兩行,我便將回條掃描下來,再用電腦將意見欄的行數增加,這樣大家就可以多寫一些意見進去。」
他相信,抗爭的每一步,都要據理力爭。








